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7 No.05(2018), Article ID:24841,11
pages
10.12677/ASS.2018.75089
The Informatics Turn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Lei Li
Law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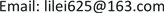
Received: Apr. 23rd, 2018; accepted: May 7th, 2018; published: May 14th, 2018

ABSTRACT
Science of law is a highly practicable subject. Its goal is to safeguard the justice, order, freedom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society. Legal research in any field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trial. Legislation and trial are the direct means to achieve these values. Legislation and trial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world of material and the non material world, so the two are not the traditional “hard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legislation and trial more rigorous and accurate, jurist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nonmaterial worl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ve been encountered in the practice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in the long term. We try to use the 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cs to gradually smooth away the difficu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cs, we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law methodology, and explore the two informatics characteristics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cs, and explor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ystem and methodology of information law.
Keywords:Legislation, Trial, Legal Information Science
立法与裁判的信息学转向:方法论及其运用
李蕾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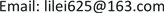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8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18年5月14日

摘 要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价值目标是维护整个社会的正义、秩序、自由与效力。任何领域的法学研究最终都要落脚于立法与裁判。立法与裁判是实现法学价值目标的关键手段。立法与裁判既关注物质的世界也关注非物质的世界,所以二者都不属于传统的“硬科学”。法学家要使立法与裁判更加严谨、准确。他们还需要关注非物质世界之中的信息科学的世界。本文从立法与裁判在实践中长期遭遇的各种难题与困境出发,以信息学视角发掘立法与裁判这两种技术的信息学特征,运用信息学的方法论与技术逐步梳理立法与裁判之中的信息现象。以信息学理论重塑法学方法论体系,回应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并尝试建立一门独立的信息法学学科与专业的信息法学研究工具。
关键词 :立法,裁判,信息学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立法与裁判为何不是“硬科学”
1.1. “物质”并非立法、裁判研究的唯一对象
所谓“硬科学”,多为单纯对“物质”进行研究的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就属于此类学科。“硬科学”的特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属性与运动轨迹相对具有规律性与稳定性。例如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化学中的质量守恒定律等。
立法或裁判不是单一以“物质”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法律”、“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法律”、“法律现象”既有物质性,也有非物质性。物质性表现在:立法条文均以文字符号表现出来,文字符号是有形的、物质的、可视的,实证主义法学家研究这些符号之间的排列与结构。作为法律主体的自然人,以“身体”这种物理形态而存在;法律的关系的客体绝大部分形态是物质的,如“动产”、“不动产”等。法律行为是以看得见的物理运动呈现出来的。例如:当侵权行为发生之时,人的财产或人的身体会发生物理上的改变。
“法律”、“法律现象”的非物质性表现在,如:法学家要对文字、符号所表达或隐藏的信息含义进行研究;人的行为受意志因素、社会历史文化、所属群体所支配、控制。人的智力活动成果附着在物质载体之前是以非物质形式而存在的;非物质形式的财产非常普遍;人体会受到非物质形式的精神损害。立法活动就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现象背后规律,并制定规则的活动。裁判就是裁判者为呈现在眼前的物质现象或非物质现象进行量衡的活动。
1.2. 立法或裁判没有精确且恒定的“公式”
物理学中的物质运动规律相对恒定且稳定,一旦有开创性的公理性发现,这些公理、公式可以运用很多年。立法、裁判却不像物理公式那样精确可量化,它变化频繁。立法与裁判的过程不能运用数理原理进行逻辑演算,在这个领域只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原则”、“要素”、“规律”或“宗旨”。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的“公式”是用数学符号来表示的,具有普适性,同类相关问题出现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演算和计算。立法与裁判的规律无法通过纯粹的数学符号来表达。数学符号也无法成为法律规则或裁判过程的主要载体。但这并不代表立法与裁判没有规律性,这些规律性隐藏于法律符号、文字、条文之后。例如:法的要素 = 规则 + 原则 + 概念。这三者要素是对千变万化法律条文的抽象表达,虽然它不是数学公式,但由于其具有规律性,其实是一种对法的要素进行抽象整理之后的推导结果,它以文字加符号为载体表达出来。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设计过法治的“要素”:“法治=普遍服从 + 良法” [1]。这个“法治要素”在几千年前形态与现在的形态完全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始终不断处于演进且自我更新之中。法理学家不断修正与改写这个“法治要素”。20世纪的美国法理学家将“形式法治”公式概括为八项原则 [2]。21世纪世界正义工程再次改写了“法治要素”的内容将其表述为九项要素 [3]。人类对法律规则的原则与要素、法治的原则与要素的探索人类永远不会止步,立法、法治的原则与规律会不断持续更新。
有人认为司法裁判相对于立法具有一定稳定的思维逻辑。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司法裁判公式的设想。例如美国法学家弗兰克教授认为司法裁判有“神话公式”与“现实公式”之分。神话公式为:R × F = D,R (rule)代表法律规则,F (fact)代表法律事实,D (decision)为判决结果。现实公式为:S × P = D,S (stimulus)是围绕法官与案件的刺激,P (Personality)为个性,D (decision)是判决结果 [4]。R是相对稳定的要件,但是S、P非常不稳定,这样就会导致最终裁判结果D不确定性。
这里的“公式”显然不是数理科学中的“公式”,它们仅仅是对司法裁判程序、步骤、规律的一种总结,我们把它比喻为“公式”,但它依然不是真正的“公式”,它们无法进行数学运算。因此,无论是立法还是裁判都是没有演算公式的,我们对立法与裁判中涉及的非稳定性因素的规律总结,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协助,这些学科不是数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生物学,而是信息科学,信息学既有对符号、文字信息学的研究、也有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信息学研究。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神话公式”与“现实公式”,其实每一个符号背后都是信息现象,运用信息学的视角能使我们对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进行更为精确的观察与分辨。
2. 法学方法论的转向与“信息主义法学”的独立
2.1. “信息”也是立法与裁判的研究对象
世界是由物质与非物质构成。立法与裁判活动没有恒久稳定的公式,那是由于这两种技术对非物质现象的掌控能力较为弱小,这些非物质现象的最大特点是观察困难,逻辑表述困难。这些原因使立法与裁判具有极其的不稳定性。随着我们对理论信息学的借鉴与反思,这些非物质现象大部分属于信息现象的范畴,如果了解信息现象的变化规律与结构。法学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会相对减弱。
立法意味着立法机关对信息进行支配与操控的一种能力。立法与裁判都关注整个人类个体运动信息或群体运动信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形下,立法与裁判效果均会受到较大影响。立法调研报告内容大部分是对信息的总结与归纳。
在司法裁判中,法官除了对法律条文信息、司法解释信息进行足够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对案件事实所呈现的信息进行掌握。裁判书只是对法律规则信息、案件事实信息、当事人信息、法庭审判过程信息的一个总结。
我国的法学体系、立法体系、司法裁判体系其分类是依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进行划分的,不同类属的立法、裁判,其研究的信息内容有所差异。宪法与行政法研究的信息类型有:国家机关权力机构组织信息、政府公开信息、公民信息、国家自然资源分布信息;民法研究的信息有:不动产物权信息、动产物权信息、人身关系信息、人的名誉荣誉信息、法人信息、组织信息;刑法研究的信息有:犯罪人行为信息、心理信息、犯罪率信息、犯罪地理分布信息、监所执行处罚信息、刑释人员的回归社会状态信息。这些信息的类型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以信息学分类的视角来看,这些信息就是:自然信息、社会信息、人文信息。其中社会信息占据了很重要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其分类为生命信息学与非生命信息学。
信息学研究者们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将人设想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其输出的信息支配与控制着人的行为。这个信息系统只要一直处于运作之中,那么他将不断处于知识的更新,自我学习、创新的过程之中 [5]。因此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同时也研究人脑产生的信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的科学。
2.2. 法学方法论的瓶颈与立法、裁判的症结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其的标志就是方法论上的独立。法学方法论与立法、裁判之间的关系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立法与裁判涉及了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各大部分法。各大部分法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构建理想的立法、精确的裁判、完善的执行。本文的研究重心放在“立法与裁判”二者之上。因此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如果理论所涉及的方法论无法应对立法与裁判中的症结,那它就是无效的法学方法论。
早期的法学方法从哲学中的方法论中吸取和借鉴而来,即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方法 [6]。“实证分析”方法注重描述法律“是什么”,运用实证分析技术进行立法与实践,这一方法技术可以一直追溯至古罗马的注释法学派。这种研究方法被后世法学家进行完善与扩充之后,逐步发展为独立且专业法学方法论。此外,还有一种法学方法论思潮与实证主义法学有部分交汇,它就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强调实在法秩序的稳定与权威,并对实在法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7]。这种法学方法在人们对实在法的精确适用上发挥了重要贡献。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法律的适用中会大量使用到“法教义学”方法论。他们不仅要深入理解实在法条文中的具体含义,还对实在法的体系不断进行梳理与总结。
价值的分析方法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侧重对法律规则的价值分析。更关注形成规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人作为主体与外界的自然性或社会性联系,外界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注重法学的终极目标与动力。随着宗教的除魅,自然神、人造神的退场,学者们对科学理性方法论的强化,价值研究方法论因此在法学界被强调的并不明显。法学家们转战于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进行结合研究。这种冲破法学学科壁垒的研究思路被中国的法学研究者描述为“社科法学”。(“社科法学”这一名词是我国著名法学家苏力于2001年所提出,即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对法学进行研究。曾经使用的名称还有:“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这种法学研究方法包罗万象,横跨多宗学科研究方法。超越了传统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于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成为法学研究方法论擂台上的两大主角,但无论是“社科法学”还是“法教义学”依然无法把控法律现象之中的非物质现象。
立法条文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保守性,其内容相对于信息时代总是相对落后,因此它对社会行为的调整往往不连贯。这种滞后性是所有国家的症结。立法困境体主要现在:第一,立法程序透明化困境;第二,回应式立法模式的滞后性;这些困境是传统法学方法论无法应对的难题。裁判的困境在于:第一,传统法学方法论会陷入无力指导法官裁判的僵局之中,相同的法律规则、概念对不同裁判者传递的信息并不对称,裁判依旧存在误差;第二,裁判者、当事人的事实认定误差;第三,不确定外来信息因素对法官、当事人的干扰等。
2.3. 法学方法论的信息学转向
法学的研究方法论的更新与成长始终没有停止,它随时可以接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目前,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未涉及信息科学领域。在国家学科专业门类的划分体系中,信息学归属于工学学科这个大类。信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体系自19世纪中叶诞生。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为各类信息,从简单的信息(如“是”、“非”逻辑判断),到复杂信息(人脑信息);从非生命信息(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信息),到有生命信息(如:生物遗传信息)等等 [8]。由于信息科学中信息类别的包罗万象,那么属于法学学科的信息也属于信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些信息包括法律条文信息、法律行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法律事实信息、法律历史信息、法律思想信息。
信息学方法论经历过“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9] 阶段。前种研究方式注重研究者与信息的互动,通过对信息的长期调查分析获取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后种研究方式侧重对信息的可量化部分并进行计算,后种研究方式过程中产生了信息熵、信息负熵等理论。
我国学者将信息的发展规律总结为:“信息不守恒”、“信息与时俱进”、“信息增长没有限制”三大定律,对法信息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条文也是逐渐扩充增加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立法条文的数量以及信息含量也在不断扩充之中。
理论信息学的总体研究方法论为“信息涌现论” [10]。在单个信息学领域内,又存在各自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如在通讯、控制、计算领域内的方法论就有:香农通讯模型、维纳控制模型、图灵模型、冯诺依曼计算模型等 [11]。人对信息进行统计、计算过程中的成与败、效率,是依靠硬件结构模型与软件结构模型,其中软件结构模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需要研究者对信息进行观察、实验、假设、推理中探索信息能够涌现所形成的模式或模型。我们需要研究信息本身的结构,还有信息的动力学原理。
信息结构与其运行的模型可以作为立法、裁判的的方法论。立法与裁判的研究范式可以从传统的对条文、概念、原则,事实、证据等转向对信息本身进行研究之上。立法条文除了是物理意义的符号之外,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既然它属于信息的类型,它必然拥有所有信息所具有的共同的结构或动力学规则。以前的立法者更多关注人类的社会关系,拥有信息学方法论视角的立法者眼中看到的就是信息。
在法庭审判上,案件的事实具有相对性与偶然性的,案件的证据除了具有物理、声像,气味等特征还具有信息学特性。掌握了信息学方法论的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是采取信息学的视角,法官所掌握的信息多寡,法官对案件信息的提炼、整理、总结必然影响着案件的判决结果。我国著名学者李宗荣教授曾经提出过“信息能”的概念。这种能量的形态是抽象的,它与物理能交错在一起。如果“物理能”能够推动物质运转的动力,那么“信息能”决定着物质运转的轨迹与方向。人的法律行为中既有物理能在发生作用、同时也有信息能在发挥作用,“信息能”同时也是推进立法进步、裁判公平且严谨的一种重要力量。
2.4. “信息法学”的独立与界定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发现法学与信息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高度重合。信息学方法论可以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因此两门学科的融合是学科发展潮流的必然。一旦两门学科结合,那么“信息法学”既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也可以作为信息科学的分支学科而独立存在。甚至每一个独立部门法学科都可以创设一个相关联的法信息学专业。
在此,我们要界定信息主义的含义。法信息学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其称为 “信息主义法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过“信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2]。当时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法”,当时“信息法学”的任务是揭示“信息法”的特征、本质。所谓“信息法”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一种法律分类,它是一种特别法,这个特别法调整与信息领域有关的法律关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前提是其研究对象的确定。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90年代的“信息法学”的建立,其研究方法都仅仅局限在管理学与法学的方法论之中。研究对象依然离不开“法”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今天所界定的“信息法学”或“信息主义法学”研究对象与方法论都是从信息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信息法”本身,而包含了法律现象中的一切信息现象。
法律、法律现象既有物质属性也有信息属性。如前文所陈述,传统法学研究对法律现象的非物质属性研究出现瓶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的价值研究。今天的信息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现象中的信息现象。因此我们对新的法信息法学定义为:对法律信息、法律信息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
信息现象不仅包括符号、数字、文字为载体的信息,还有以人的身体为载体呈现的信息。尤其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的信息现象将成为信息学与法学结合的突破口。信息法学的独立意味着我们将会突破传统法学概念的界限。对法学中核心概念将重新以信息学素语进行定义。例如:“信息人” [13] 的假说;对“人格”概念的重新定义;以信息学视角重新界定“人的行为”等。
3. 信息学视角下的立法、裁判信息运行样态
3.1. 立法过程之中的信息样态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将概念的发展及演进描述为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承继了“自在”与“自为”的术语,运用在阶级的分类之中。哲学家萨特论证过“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 “自在存在”是意识之外超越现象的存在,其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更其属性;“自为存在”被人的意识活动所牵引,它受人的有意识活动而影响。在此一系列哲学基础理论之上,信息科学界诞生了“自为信息” [14] 这个概念。在我国的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将信息的动态发展进程总结为“自在”、“自为”、“再生”三种形态 [15]。
3.1.1. 立法过程中的“自在信息”
“自在”状态下的信息还未被主体所识别。是信息最原始、客观且自在状态的阶段。此时的信息具有物质的天然特性 [16]。由于立法者需要创设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均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以立法者在做立法准备工作之前需要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自在信息”,这些信息的样本的数量越巨大,立法工作相对就越科学、越完善。这些“自在信息”包括: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信息;已经制定好的国家制定法信息。这些信息是随机、碎片化、无规则的“自在信息”。不仅如此,立法者还要接触大量的法律的理念、法学方法、法学知识、法学历史信息,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均是具有人体器官可感知的物质载体(行为、数字、文字、符号、语言、声音等)。例如:人的行为意味着人的四肢肌肉的运动过程能产生“自在信息”。立法者可以依据该信息系设想创设一系列调整该行为的条文。
3.1.2. 立法过程中的“自为信息”
“自为信息”是主体对信息的主观把握形态。人的眼、耳、鼻、喉等官能器官是人感知外界“自在信息”的接收器,神经系统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再将这些信息一步步传导给人的大脑。人脑神经系统是信息处理中心,它将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分辨。大脑中不同的神经中枢对接收信息进行辨识之后,形成感觉、知觉。这些感觉知觉可以被人脑存储、记忆下来。因此“自为信息”第一种形态就是“自在信息”通过人脑被“辨识”之后状态;第二种形式是“自在信息”变为人脑可存储可记忆的状态。这个状态下的信息已经不再具备“自在信息”时可以明显感知的物质属性,而具备一种的弱感知的物质属性。之所以我们暂时认定“自为信息”具备弱物质属性,那是因为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法具体、精确读取人脑神经系统内部存储的信息。
“自为信息”状态是立法环节中最难以把握的阶段,立法者需要对“自在信息”进行感知提炼、总结。立法“自为”状态的信息是经过立法者人脑神经系统进行语法、翻译、转换后的信息。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和“观念”不仅受到立法者人脑构造的影响,更受到立法者,教育背景、文化背景、认知,价值判断、道德修养的影响。对不同的立法者接收相同的自在信号或者符号,并不能形成完全相同的“自为信息”。例如“权力”这个字符,拥有不同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立法者对这个字符读取后的自为信息表达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立法会存在争议的缘由。
3.1.3. 立法过程中的“再生信息”
立法者对“自在信息”进行辨识之后,立法者的大脑神经系统对信息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法律条文要素的“自为信息”,法律条文的各项要素包含:规则、原则、概念。这些“自为信息”最后通过文字、符号这些载体表达出来。这就是立法过程之中的“再生信息”。
“再生信息”是信息被立法者改造、被创造后的形态。是立法者大脑对“自在信息”进行主观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个“再生信息”可以继续停留在人脑神经中枢之中,也可以运用符号、数字等物质载体表达出来。当“再生信息”有了物质载体,它又将成为新的“自在信息”。它将继续被人脑所感知,由此而进行不断的循环。立法更新过程与信息再生过程是不完全同步的。它们是交错进化的。
新立法条文是“再生信息”,新的立法原则也是“再生信息”。这些符号与文字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立法者对人脑意识产生的法律规则信息进行处理后所凝结的产物。这些承载着立法者新的意识的信息符号、文字,它们既维持着现实社会的秩序,也是未来新的立法者创造更新新律条的起点,新律条的产生意味着信息又回到“自在信息”这个起点。新的立法规则裁判判例又反作用影响未来社会的信息发展方向,这一些列动力学过程不断在循环往复地重复着,立法裁判与信息他们共同交错着、进化着、演进着。立法的整个过程就是“自为信息”、“自在信息”、“再生信息”相继出现、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人作为主体与不类型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3.2. 信息识别、干扰与司法裁判误差
审判界饱受诟病的问题为判决尺度与标准的不统一。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有普遍性。司法裁判不是精确的数学计算。相同案件不同的法官裁判结果不可能像数理符号那样一致,我们只能力求在一个相对区域的一致。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也并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判决结果。但是人们对司法裁判的质疑之一就是案件裁量标准的不统一。影响司法度量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司法非独立性因素、司法腐败腐败因素,在本文中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二者因素,而专门探讨信息对裁判者的影响。
3.2.1. 法律条文、概念传递的不确定信息
即使最清晰的立法条文还会出现概念或规则的模糊区域。在刑事条文中,经常会出现模糊的概念,如:“足以”、“严重危害”等词语,这说明这个中文字符不能表达精确的信息,法官在接触这样的概念会有无措感。法官此时需要发挥主观作用,推测立法者所要最终传递的立法信息。以往我们将这种信息描述为立法精神。生物学将“精神”描述为人体大脑释放的“能量”。当我们接触过理论信息学之后就会明白,这个“精神”的含义其实就是“信息”。
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提到了“自为信息”的概念。在法官审判环节,同样存在着“自为信息”,每一个法官“自为信息”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不同法官面对的法典是相同的,但他们对法律条文背后信息含义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成文法国家尤其重视裁判者对法典所表达信息的精确传达。为了应对法典概念的理解冲突。于是法学家们创设了另一种立法模式——命名为“法律解释”。但是即使有了明确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法律条文毕竟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概念与规则,这种信息是无法还原人类所有的行为,它只能对人类社会行为之后的信息进行抽象地概括。此时的审判还需要其他法律信息的补充才能更加接近裁判的真谛,这些信息就是过往的已经审判过的案例信息,在英美法系被称为判例,只有法典信息,审判信息越具体法官的裁判才能更加科学且精确。
3.2.2. 裁判者对案件事实信息的判断差异
法庭上所被呈现的法律事实,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些案件事实既有当事人通过语言、声像传递案件信息的言语证据;还有以物证、试听资料等物理方式存在证据。这可视、可听、可触的证据都是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裁判者更加关注的是案件事实信息本身。法官不仅要面对真实证据呈现的信息,还需要面对真伪不明的证据呈现的信息。
除了案件事实信息,裁判过程中还会生成经过人脑进行处理、归纳过的信息,如:书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它们以文字符号为载体。一般来说,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视频资料对现场信息的还原度是最高的。其他类型的证据,如:言辞信息、物质载体传递的信息,都不足以单独还原现场信息。这就需要法官对每个证据所呈现的案件信息进行关联度的判断。
裁判者法官除了对当事人外在法律行为的进行还原,还需要研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信息。传统的司法裁判者更加注重行为人犯罪时的行为信息。对行为人主观善恶的划分较为笼统。有学者为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研究人脑是如何驱动人的行为,从而研究人的神经元系统。国内外不少跨学科学者也正在进行法律神经学的研究,并将法律神经学 [17] 视为一种交叉学科。脑神经的专家研究神经元结构与机能,这其实也是在对大脑的内部物质进行研究,以信息学视角来看,信息学家更关注被人脑神经元输出或输入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专业法医学的鉴定,测谎仪的检测。
测谎仪是对当事人心跳、唾液、血压、面部微表情的信息分析,最新的技术中还引进了神经彩色影像信息,核磁共振影像信息。这些信息均可弥补案件证据所呈现的信息不足,但是测谎仪所展示的信息结果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因此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但是它可以作为侦查环节中的线索信息。神经监测信息对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给了具体的参照,这使得精神损害赔偿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3.2.3. 外界信息对裁判者的干扰
法庭裁判之外的干扰信息有很多。第一类信息是其他权力机构所传达信息。其他权力机关有:党政机关、国务院及所属部门等行政机关、上级审判组织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考虑法条所传递的信息还会考虑国家政策信息,党政机关的参考意见,上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先例,这些信息有的是影响司法独立的,有的是法官可以借鉴并参考的。第二类是人情关系诉求信息:中国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法官不是被隔离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亲属,朋友,会接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情诉求信息,这些诉求信可能是亲朋好友发出,也有可能是上级领导发出,也有可能是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发出,这些信息对司法公正有不良影响,我们仅有的回避制度还不足以扼杀这种不良信息,第三类信息是法庭审判中的意外信息:当事人的激动的情绪引起的愤怒举动,律师对法庭裁判不满的粗暴言论或动作。第四类信息是媒体和舆论信息。舆论与新闻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力,它与传统公共权力有共通之处,二者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一定支配力量,公共权力的支配力量是物理化的,新闻与舆论的支配力量是信息化的,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能”,它通过语言,声像,符号进行传播,这种“信息能”立法者,对裁判者都是有较大影响的,尤其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非常容易收到法庭之外的舆论信息干扰,中国的药家鑫案,美国的谢帕德,都受到了媒体信息的误导 [18]。
这四类信息是可以运用信息学的理论与技术采取信息屏障工具对不良信息进行屏蔽。相信信息学技术足以应对这个难题。
3.2.4. 当事人的信息采集能力差异
司法裁判结果不标准、不精确、不统一的,并造成较大误差的原因还有当事人“信息采集能力”的差异。当事人大部分均是非法学专业出身,他们没有系统学习过证据学的相关知识,在法律行为产生之时他们也不会意识到对可见证据进行严格的采集,更何况用信息科学学的视角来看这些证据。
如果我们将事人这个群体的差异性与法官之间差异进行比较,显然前者的差异性更大。证据采集的过程其实就是信息获取的过程。有的人或许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通过自学也可以采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或通过技术手段获得更详实更具体的数据,有的人文化素质不高,普法度不强,
有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取的信息更详实更科学,有的人获取的是无效信息、不相关信息,甚至是误导性信息,法官在面对不同当事人已经呈上的信息上就形成了不同的事实判断了。
这也不难理解,同样一个类型的案件,有不同当事人获得不同的裁判结果了。
4. 立法与裁判的信息学工具
4.1. 立法、裁判、信息源采集器
信息就像矿山或石油一样珍贵,如何探索以及挖掘对立法、裁判者有效用的信息资源非常重要。我们根据开放程度将信息分为两大类别。
第一类信息是共享信息源。百度、google这些网络搜索引擎,就是这种类型信息源的采集器、探测器。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是输入字符。通过此类平台搜索的信息,但是即使搜索到信息,均是没有经过提炼打磨的无规则、无逻辑的信息,他们是信息的堆砌而已。其中还包含大部分的无效、干扰信息。
专业法律数据库其实与普通搜索引擎的性质是雷同的,它们其实也属于共享信息,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共享。它较普通共享网络搜索引擎的优势在于:在这些数据平台可以获取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信息,立法规则、裁判信息,这些学术数据库对专业法律信息进行了学科门类的精确分类,者让法学研究者的信息采集效率提升不少。
第二类信息是私人信与保密信息。这部分信息非常珍贵,同时也会难以获取。如:关于私人电话,家庭住址信息,大量集中在快递行业网络平台之中。私人消费数据大量存储于网络购物平台中,私人通讯信息存储于联通、电信等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器之中。还有民营企业、政府机关、事业机关的人事、财务状况信息。这些信息任何机构都不会轻易向外透露,并且会逐渐形成“信息寡头”、“信息垄断”的局面。如果第三方需要获取这样的信息,他们也许会通过秘密买卖的方式进行。如果这些信息能够作为立法与裁判的共享信息,许多难题会迎刃而解。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有先例,如:在执行判决结果领域,为解决失信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的难题,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与淘宝等互联网企业合作找到被执行人的真实居住地址。
这二类信息即使获取依然还不能应对立法与裁判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碎片化、未过滤的信息,社会法律关系或当事人社会关系信息的完整表达。尤其是公共平台的公开信息搜索引擎对信息之间的联系、信息主体的社会关系谱探测不够深入。于是许多计算机学者开始研发新型的信息探测技术,关键是寻找信息之间的联系与规律。有搜索引擎的设计开发者研究一些以社会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搜索引擎,例如200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了一款“人立方” [19] 搜索引擎,它能够从巨量网页信息中抽取人的姓名,所在地,所属机构等信息,让后经过关联度运算,描绘出较为详细的人际关系图谱。设计者将信息结果呈现得更加形象化,尽量用图画的形式对人物的社会关系进行表达。图画信息传输速度较文字更为直观,效率更高。虚拟货币比特币出现之后,“区块链”技术又再次更新了数据库等信息技术,并掀起了异常数据与信息的革新,这意味着信息可以采取一种防伪技术加以保证。立法与裁判者可以回避虚假信息与伪造信息。
4.2. 设计立法、裁判信息检测仪
立法与裁判如同产品,它们也有优劣之分。此时国家需要一套完整的质量检测工程来对立法与司法裁判结果进行质量评估。合格立法与裁判质量工程体系建立的关键一环就是“信息检测仪”。如果说信息采集是“挖矿”,那么信息检测就是对粗矿进行提炼与分析,并分析矿产物质结构、纯度与精度的过程。这个信息检测仪作用如同物理学放大镜,化学的化验工具。
立法与裁判的道德价值有自由、平等、秩序、人权、公正,这些是相对稳定的立法目标,这些目标、原则就是衡量立法与裁判是否合格的质量指标参数。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已经将这些价值公式转换为数据指标模型,如:法治指数指标。即信息的比对指标已经设置好了,这样的指标参数模型,全球等各类组织已经设计好多种类型,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等等。但是接下来是如何来设计一个检测仪。这个检测过程就是将各国立法、裁判信息与全球标准法治指数要素进行比对,然后进行评分的过程。这过程以前由人工评分完成,如果全球信息化程度较高这个过程可以由人工模式转向非人工程序化模式。非人工程序化模式评分体系结果会更加客观。
在正式评分的过程之前我们又会回到上一问题,即“信息源”的问题,这个信息源对信息检测仪来讲称为信息“样本”。良好的样本会让检测结果的更接近真实情况。良好的评估结果需要信息探测器与信息检测仪同时工作、完美配合。
立法的信息检测领域有很多,例如:如果检测仪检测一国基本人权之中的工商业人权发展状况,就需要信息探测器深入到企业内部进行工资信息的收集;对员工工作时间的信息进行收集;对员工工作环境的信息进行收集。再如:衡量一个国家的裁判程序正义实现的程度,就需要对法庭庭审过程信息进行收集;对当事人进行问卷反馈信息收集。这些信息都大量涉及到我上述正文中提及的第二类保密与隐私信息,它们的获取难度非常大。国家必须建立专业化的特殊信息共享平台,国家机关或研究者等特殊人员才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访问与采集,并须签订严格访问协议与保密协议。除了平台的建立。对那些信息死角也要进行全面的发掘,这些信息是没有连接到任何信息网络平台的,如:没有摄像头的街区所产生的社会行为信息;没有被登记过动产流转信息、所有人信息,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变更的事实信息等等。但是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又会出现对公民个体隐私权的侵犯,这会造成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利益相冲突的困境。这个问题也是将会被很多法学家所探讨。本文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也会持续关注这些法信息学困境并探索最佳的解决方案。
文章引用
李 蕾. 立法与裁判的信息学转向:方法论及其运用
The Informatics Turn of Legislation and Trial: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5): 579-58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5089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M]. 郑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 李蕾. 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J]. 时代法学, 2012, 10(2): 25-30.
- 4. 弗兰克•H•奈特. 集体决策的理论根据[J]. 政治经济学杂志, 1938(12): 860-869.
- 5. 李宗荣, 田爱景, 吴晓凌. 信息能: 构成宇宙的第四要素[J]. 中国医药卫生世界信息, 2002(1): 401-404.
- 6. 刘水林. 法学方法论研究[J]. 法学研究, 2001(3): 42-54.
- 7. 王泽鉴. 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8.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论[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9. 陈向明.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6): 93-102.
- 10.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论[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11.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 概念、原理与方法(V/VI) [J]. 医学信息, 2005, 18(4): 409-419.
- 12. 马海群, 何延辉. 再论我国信息法学的学科建设[J]. 情报资料工作, 2002(5): 17-21.
- 13. 李宗荣. 信息心理学: 背景、精要及应用[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 14. 邬焜. 论自为信息[J]. 人文杂志, 1986(6): 55-60.
- 15. 邬焜. 哲学信息论的要略[J]. 人文杂志, 1985(1): 37-43.
- 16. 邬焜, 夏群友. 再论自在信息[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2, 29(2): 8-12.
- 17. Taylor, J.S., Harp, J.A. and Elliott, T. (1991) Neuropsychologists and Neurolawyers. Neuropsychology, 5, 293-305. https://doi.org/10.1037/0894-4105.5.4.293
- 18. 李蕾. 正义女神是否应当遮住耳朵[N]. 检察日报, 2012-04-05(3).
- 19. 高钢. 绘制人的社会关系信息图景的尝试及意义——“人立方关系搜索”预示了什么[J]. 国际新闻界, 2009(5): 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