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
06
No.
04
(
2018
), Article ID:
27737
,
8
pages
10.12677/WLS.2018.64020
Analysis of Ruan Ji’s “Open Mind”
Peiyu Guo1,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Wuhu Anhui
2Jieshou City High School, Fuyang An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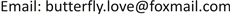
Received: Nov. 6th, 2018; accepted: Nov. 20th, 2018; published: Nov. 27th, 2018

ABSTRACT
Ruan Ji’s thought of “Open Mind”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was a result of his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his life. In essence, the spirit reflects the frustration deep in his soul, which is also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The influence of Ruan Ji’s thought is wide and profound, but due to the time and personal reasons, it has limitations that cannot be surpassed.
Keywords:Open Mind, Ideological Origin, Spiritual Essence
解析阮籍的“放达”
郭培玉1,2
1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界首中学,安徽 阜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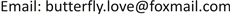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6日;录用日期:2018年11月20日;发布日期:2018年11月27日

摘 要
阮籍的“放达”思想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是对他自己矛盾人生哲学思辨的结果;在精神实质上折射出其灵魂深处的失意情结,同时是其强烈生命意识的流露。阮籍的“放达”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又有其无法超越的局限性。
关键词 :放达,思想渊源,精神实质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阮籍是正始时期的名士代表,他才学横溢,为“竹林七贤”之领军人物,同时他又以行为超常、狂放不羁而著称于世。《晋书·阮籍传》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 [1] , P. 204)《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篇目单独介绍阮籍“放达”的事迹,其中“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步兵校尉。”条目刘孝标引文士传曰:“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官。”另有“晋文王称阮籍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籍)宏放不羁,不拘礼俗。”( [2] P. 205)可见“放达”一词可以概括为阮籍最显著的性格特点,由于思想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处世观,故“放达”亦为阮籍独特的处世方式,即“放达”观。关于阮籍的“放达”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誉之者称之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贬之者则认为是消极颓废,伤风败俗,分歧之大,竟到了截然相反的程度。阮籍作为一个从小就博览群书,饱受儒教熏陶的封建文人为何会表现出如此狂态呢?同是傲睨群伦,嵇康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阮籍却终得天年;同是纵酒放达之人,与刘伶相比,阮籍的“放达”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并在当时形成了“放达”的社会风潮。总之,阮籍的“放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从阮籍“放达”形成的思想渊源、精神实质进行探析,以求对阮籍“放达”有更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
2. 阮籍“放达”的思想渊源
阮籍身处魏晋易代时期,他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影响。主观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对抗及主观世界内部各种思想的激荡,使阮籍的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其中儒与道,仕与隐的矛盾是贯穿其生命始终的主要矛盾。阮籍的“放达”是他企图平稳思想冲突的思辨结果,也是他矛盾情绪的变相发泄。
2.1. 儒与道的矛盾,使他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
阮籍的思想中存在儒、道两方面的矛盾,儒、道两种哲学观念一直在左右着阮籍思想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思想主流经历了由儒到道的转变,受其思想主支配,其处世态度也在发生着显著的改变,这对阮籍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起着重要作用。“名教”即“礼教”,是指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被看作是全部秩序的基础,属儒学范畴;“自然”是指老庄崇尚人性的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保其天性,自由自如,不受拘束。“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阮籍等“竹林七贤”的思想主张,即是从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中解脱出来,做一个本色的真我。
阮籍出身于陈留阮氏家庭之书香门第。阮氏家庭世奉儒学,籍父阮瑀受业于汉末学者蔡邕,为“建安七子”之一。受家学渊源的影响,阮籍早年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向往儒家大贤的性格情趣。阮籍曾对早年的生活总结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3] , P. 21) (《咏怀十五》)由于儒家思想由外在的社会群体意识逐步内化为阮籍内在的个体意识,并进一步成为他人生观,世界观的核心,所以阮籍早年满怀着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如其《咏怀三十九》中所表白:“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身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3] , P. 48)此诗基调慷慨激昂,突出表现壮士垂功名、彰忠义、立气节的儒家品格,流露出自身的理想和追求。
齐王曹芳在位期间,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两大当权集团长期以来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大肆残杀异己,致使大批文人死于非命,眼前血淋淋的现实使得阮籍的建功理想和英雄主义趋于破灭,他的信仰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开始对原来的儒学观念产生了怀疑,其《咏怀六十》( [3] P. 73)在大篇幅描写了“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的儒者后,以“老氏用长叹”收笔,说明此时阮籍已逐渐用老庄思想来消解以前的儒家思想,需要指出的是,阮籍少年就受到老庄的影响,但那时由于儒家观念在阮籍头脑中先入为主,所以阮籍总是不能干脆地脱离早已建立起来的儒家人格理想。此时,儒与道两种哲学观念在阮籍的思想中产生了极不调合的矛盾。阮籍的思想在儒与道的矛盾中挣扎,他的思想意识在矛盾思辨中痛苦而又彷徨,于是他的行为开始异常起来: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恪守儒家父子之纲的他也竟口出狂言:“杀父乃可!”这些“放达”之举是阮籍对于司马氏假仁假义的黑暗统治的激烈控诉,是对无道社会现实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无奈反抗。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齐王芳而另立贵乡公曹髦,由大臣废立皇帝,这表明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司马氏夺权篡位之心已昭然,传统的礼教此时已变质成为毫无价值的虚伪之物。此事件给阮籍的政治热情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于是道家思想在他头脑中逐渐居于主流,于是他开始换一种视角看待人生,尝试着摆脱所谓名教的圈囿。他用“放达”的举动来平衡内心道与儒的冲突,于是他在文章中塑了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自己——“大人先生”,他借“大人先生”之口痛骂“礼法”之士;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 [2] , P. 392)这种激愤之语,其实是对违背理想原则的现存“名教”的批判和否定。披着“名教”这样一件“道貌岸然”的虚伪外衣,却干尽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是为阮籍所不耻,他宁可超越这道他以前奉为至宝的精神藩篱,而去追求一个纯真洁净的自我,从而达到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精神境界。
儒与道的矛盾是阮籍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这种矛盾思想的指引下,阮籍毅然走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境界。
2.2. 仕与隐的冲突,使阮籍做出了纵情背礼的“放达”行为
仕与隐的冲突始终贯穿于阮籍的一生,这种冲突也导致了阮籍做出纵情背礼的“放达”行为,也就是说阮籍从以仕为荣,立志治国平天下转到不乐仕途,求官只为美酒,为官不与世事等种种前后相悖的纵情背礼的“放达”之举从这里也能找到根源。
作为一个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阮籍“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咏怀六十一》) ( [3] , P. 74)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立金石之功,他的志向是在王正其德,公守厥职,上下不疑,臣主无惑的理想社会中干一番大事业,但现实却是失刑者严而不检,丧德者高而不尊,这使得阮籍的济世之志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史载他曾登临广武城面对楚汉的古战场,发出愤世的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1] , P. 202)动乱的时局没有给阮籍提供一个理想的政治舞台。政界的尔虞我诈,伪善无耻都使阮籍对现实深深地失望,出仕对于阮籍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他只想在这浑浊纷争的乱世之外寻找一片净土,隐居起来以尽天年,远离政治是非,以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他找来几位朋友“嘉平中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陶潜《群辅录》)他们终日纵酒放荡,谈玄论道,以“放达”示人来发泄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然而,司马氏一方面为了巩固其政权,积极拉笼天下名士,以显示自己篡位的“顺天应人”;另一方面因为其统治权多是通过诡诈之术得来的,所以很忌讳文人们聚集议论他们的行为。于是司马氏下令砍尽竹林,不给阮籍任何退隐的余地,逼其出仕。内心淳真向善的阮籍面对阴险残酷的司马氏集团,只能选择出仕。
阮籍的仕途在司马氏的“庇佑”下一路平坦,纵观其一生,他曾历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大将军从事中郎、步兵都尉等职。仕途通达是阮籍少年时的梦想,按讲他应踌躇满志,一展抱负才是,但此时他却郁郁寡欢,激情全无,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出于对前朝君臣之义的道德规范,使他始终不能接受司马氏集团,他兼济天下的责任感无论如何不能依托于司马氏政权来实现,他出仕实出于违心。孔夫子也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在无道的社会中,阮籍身置堂,却心向山野,隐逸的念头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辞仕不能,隐居不得的现实使得阮籍的心灵在仕与隐的冲突中倍受煎熬,他在这种心理冲突中苦苦寻求着一种平衡的途径,于是释学在家居士,仕隐兼修的理念使得阮籍豁然开朗,隐逸未必非得出家,也未必非得得到山野中去。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一样能达到摆脱羁绊,通达自由的境界——大隐隐于朝,于是阮籍采取了“仕而朝隐”的处世方式,即虽身在仕途,却再也无意于功名利禄。为远纷扰,一方面他“为人至慎,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2] , P. 8)不再发表自己的治世议论,另一方面他又目无纲常,纵酒放达。于是他开始“为官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只因“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数百斛,乃求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1] , P. 201)这种放达的行为在世人看来,实属纵情背礼。
“仕而朝隐”的双重生活态度构成了阮籍独特的隐逸人格,这种隐逸人格既表现为主动出世与被动抗世的矛盾共存,又表现为忧愤济世与淡薄遗世所并有,这些都表现在他“放达”的举动这中。《晋书·阮籍传》( [1] , P. 201)载他乐东平风土,文帝便封他为东平相,他骑驴上任,“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反映了阮籍出仕的治才,但他并没有以功自居,而是“旬日而还”表明了他朝隐的“放达”态度。《世说新语·简傲二十四》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的,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2] , P. 410)在这种严肃的场合,唯有阮籍无视礼节,箕踞啸歌,旁若无人,放达自如,这也反映了他已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的朝隐态度。
综上所述,阮籍的“放达”深受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他对自己矛盾处境痛苦思辨的外在表现。
3. 阮籍“放达”的精神实质
阮籍的“放达”表面上看起来傲视群俗,遗世独立,而在精神层面的实质上,却是其失意情绪的折射和生命意识的流露。
3.1. 阮籍的“放达”折射出其灵魂深处的失意情结
阮籍经经纵情于酒,对诗抒怀,临山长啸,不寐弹琴,失路恸哭……种种“放达”之举看似洒脱不羁,而实质上却恰恰折射出其灵魂深处的失意情结。
阮籍有着高洁的志趣和清醒的政治态度,但在险恶的政治氛围下,他既慕“高鸟”之志,又羡“凡鸟”之生,他的一生始终处于一种进退失据,孤独苦闷的精神困境中,于是他选择了酒,转向杯中物来寻求解脱。他仿佛把自己浸在了酒缸之中,以酒度日。纵酒是阮籍极度愤懑的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是对世事无可奈何的失意寄托。阮籍很能喝酒,动辄饮上二斗。《世说新语》中所载阮籍就是一个失意的醉者形象:他经常是披头散发,酗酒放达;不与世事的阮籍常与朋友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母亲去世了他照样进酒不误;葬母时他还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亲友来吊丧时,他却醉态百出;司马氏下令让他写《劝进表》时他醉眼朦胧,一挥而就……对于玩籍纵酒放达,《世说新语》解释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2] , P. 409)阮籍本想借酒浇愁然而却是酒入愁肠化作伤心泪。“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三十四》) ( [3] , P. 43)阮籍的纵酒放达,已没有曹操“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英雄豪气,更没有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超旷飘逸,有的只是“徘徊何将见,忧思独伤心”( [3] , P. 1)的孤苦和失意。
阮籍的身上同时存在着现实和理想的两种人格。阮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完善自己的人格理想,但这种努力在残酷多变的现实中是徒劳的,于是造成了阮籍心灵上的失意情结。在酒的作用下,这种失意情结得到显现,放大,使他处于失去适当的人格定位,迷失自我的状态,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位纵酒放达的醉者阮籍。
阮籍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但吟阮籍的诗却很少能发现“酒”字,更嗅不到丝毫的酒气,这不能不让人置疑阮籍对酒的真正感情,同时也让人看到了阮籍另外一种放达——“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手会于风雅,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 [1] , P. 205)阮籍满腹愁肠对酒不能言说,转而寄情于诗,诗歌作为感情艺术是现实生活凝之后的一种升华,阮籍在诗中倾诉自己愤愤不平的郁懑之气,这种艺术化的发泄方式,不失为名士风流的“放达”表现。
在极度压抑,苦闷的处境之中,阮籍不得不唱,又不能高唱,只能微吟当哭,于是便创作了《咏怀》组诗,其《咏怀诗》大都是政治抒情诗,诗人触景生情,感物怀忧,表达曲折,比兴隐晦和《楚辞》有类似色彩。钟嵘曾评他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1] , P. 205-206)如其(《咏怀十一》) ( [3] , P. 16)“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这首诗以“朱华”“黄雀”暗指魏君的荒淫、无能,不知危险即将临近。诗人为魏的灭亡而掉泪,为自己失去正主而伤心。阮籍的诗歌美丽而深沉,这些不朽的诗篇纯是其失意眼泪的结晶,古人评其《咏怀诗》“正于不伦不类中,见其块磊发泄处”。( [4] , P. 178)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作者的积郁之作,是他发泄痛苦的一种方式,这些诗非常深刻地刻画了作者孤苦的心境。细读其《咏怀诗》“心”字出现了15次,“悲”、“伤”各11次,另外他的诗中还充满“辛酸”“怨尤”“憔悴”“感慨”等词语,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抽丝剥茧如茧抽丝般的郁闷和深沉博大的忧思。因此“放达”在阮籍诗歌中的意义不仅仅构成对恶势力的批判力量,也是对个体生命痛苦和不幸的把玩。读懂了阮籍的诗歌,也走进了他伤疤累累的内心世界,也看到了那凝在其灵魂深处的失意情结。
“临山长啸”也是阮籍“放达”的表现。《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嗜酒能啸”。( [1] , P. 201)可见“啸”在阮籍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啸”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三国以前就已经存在,但真正开中古“啸”风的关键人物是阮籍。阮籍的“啸”声具有特别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世说新语·栖逸十八》载:“阮步兵啸闻数百步。”不仅如此阮籍的“啸”声还特别能震撼人的心灵,故阮籍还能以啸会友,当时苏门山忽然来了一位超凡脱俗的真人,阮籍前往欲与其探讨“终古栖神道气之术”但那真人却根本不把阮籍放在眼里,傲慢得连眼珠懒得动一下,阮籍无奈,长长地啸了一声,而这啸声却引起了真人的共鸣,与阮应和之。阮籍在凶险的政治环境下压抑着自己的本性,他有志难以伸展,有口又不能辩论,长长地呼啸一声,的确能排解胸中的失意不平之气,从现代医学上讲,失意时对着空旷的山野长啸一声不失为一种排遣郁闷,找回自我的健康发泄方式。阮籍“啸傲江湖”是其“放达”的表现,亦是其失意的映射。
阮籍不仅是思想家、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精通乐器,善于弹琴。“不寐弹琴”的放达之举也是阮籍排解失意情结的一种手段,其《咏怀一》( [3] , P. 1)中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夜深人静之际,本是万物休息之时,但忧心忡忡的诗人却每每不能入睡,失眠的阮籍试着用琴声来安抚自己惆怅的心绪,音乐的世界在阮籍来可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这是他自我设计的精神乐园,但现实证明音乐根本无法拯救他痛苦的灵魂,于那凄清的琴声之中,我们也能听出诗人的失意情怀。
除上述以外,“失路恸哭”也是阮籍“放达”的重要意象之一。《晋书·阮籍》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1] , P. 202)男儿有泪不轻弹,悲声一发惊天地、泣鬼神,这哭声中又包含着几多生不逢时的辛酸与失意。“失路恸哭”是一个颇富深意的象征,凝集着一种正直文人深沉的失意情结。
传统儒教道义的颠覆,使阮籍处于依违两可的矛盾生存处境之中,在任诞不羁、漠然民情、洒脱不凡的外表下,阮籍有着一颗执着而认真的心。面对混乱的世事,阮籍怀古伤今又无可奈何,他独自一个人驾着车在天地之中纵横,不由径路的结果是“车野穷路旁”( [3] , P. 91) (《咏怀七十六》)无路可走,“中路将安归” ( [3] , P. 11) (《咏怀八》)“失路将何如?(《咏怀五》)” ( [3] , P. 7)任情的结果是在旷野中无告的恸哭。他哭,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理想抱负走到了穷途末路,曹魏正统走到穷途末路;他哭,是为自己,为国家,为天下的仁人志士。终于,他调转车头伤心地驾车返回了,荒野里留下一个失意的背影。
3.2. 阮籍的“放达”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
在阮籍的“放达”中流露出他远祸全身的求生意识和对于生命消逝的深切哀痛及对于人生理想的不懈探索和追求,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强烈生命意识的体现。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来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课题。魏晋以来,社会的动荡和黑暗更加引起士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生存的焦虑,进而激起他们生命意识包括死亡意识的彻底觉醒。他们感觉到人的渺小和可悲,人生奄忽,犹如朝露,一切道德伦理,功名富贵都是虚假的或是值得怀疑的。有的只是人生短暂和死亡进逼时的恐惧与绝望。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在危险的情况下求生则是一处生命本能的体现。生命越是短暂,越是被死亡胁迫,生存的欲望就越强烈。从辩证的哲学观察来看,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有时作适当的妥协并非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加一种勇于面对现实的坚强,于是阮籍选择了一条全身全节,不死不屈的人生之路。
阮籍的“放达”在表面看似荒诞不羁,颓废消极的背后,深藏的是对于生命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阮籍的济世梦破灭后,他极力想摆政治的漩涡,以远害全身。正始三年,蒋济任太尉“闻其(阮籍)有俊才而辟之”阮籍奉上一篇记暗中却溜掉了。结果“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1] , P. 201)阮籍侥幸躲过一劫。但司马氏并不罢休,一方面对公然持不合作态度的名士,不惜血腥屠戮,另一方面对阮籍恩威并施,阮籍只得又一次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凶险的仕途。为了远离司马氏政权的辐射,他开始纵酒佯狂,以保全性命。( [1] , P. 201)《晋书·阮籍传》载:“为回避司马氏提亲,阮籍大醉六十天,便司马氏‘不得言而止’。钟会数次寻衅,以求罪证,阮籍皆因酣醉而获免”。
酗酒伤身,但阮籍并非真醉。( [2] , P. 134)《世说新语》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空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对于司马昭的假装谦让阮籍是非常厌恶的,他不想写却又不得不写,醉意中在木札上把文章写了出来,不加任何修改就成为一篇好文章,可见阮籍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纵酒”实乃是阮步兵求生的一种智慧。不仅如此,阮籍的诗放达超逸而又曲折隐晦,同是出于求生的心理动机。李善评其诗“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 ( [1] , P. 206)王夫之评日:“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恩:意固径庭,而言皆一致,信其然但然而又不徒然,疑其必然则彼固不然。”使“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 [1] , P. 48)阮籍为了生存下来可谓处心积虑,生存是生命意识的基层需求,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死亡总笼罩在每个人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无论什么人,死亡始终是横亘在生命路途上的沟壑无法超越。阮籍对于生命消逝的悲恸则是生命意识的终极体现。阮籍对死者的哀悼,更趋向一种自然主义,不所拘于形式,更注重深层次的内心体验。阮籍“性至孝?”但得知母亲去逝时,他照样留人决赌,赌毕饮酒、食肉纵情背礼,看似超脱了生死,然而临诀时,他的悲痛之情却喷涌而出“他举号一声‘穷矣’!吐血数升,废顿良久。”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母亲的不舍与留恋能及对于死亡的无奈与绝望。阮籍对于生命消逝的感伤不仅局限于亲情之间还扩大到世间的所有的美好事物的存在。( [1] , P. 202)《晋书·阮籍传》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这是阮籍坦荡,放达的表露,他深知此才女未嫁而天,乃“天地灵秀之气一瞬即逝者” ( [5] , P. 291)他赏识其生命的美好,痛惜此生命的短暂。他之所以不顾礼节,尽兴哀悼兵家女,是出于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切认识和思考。
阮籍对生命充满着执着的爱,这正是他积极向上,坚强不息的斗争精神的折射,阮籍的一生都处于一处矛盾和痛苦之中,但只有在痛苦中他才体会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在苦难之中他才奋力绽放生命的美丽。其《咏怀七十一》表白道:“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 [3] , P. 85)这说明阮籍并没有因生活的境遇而消沉,相反他更加积极地追求生命的美好、生活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 [2] , P. 392)《世说新语·任诞》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于是阮籍便经常到她那里买酒喝,醉了,便睡在妇人旁边,“夫妇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毫不掩饰他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其中绝无任何不良的企图,可见其“放达”之中包含着对生命美好的追求和尊重。阮籍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世说新语·任诞》载:“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按当时礼节主人应陪着客人哭,裴楷对此并不责怪阮籍,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阮籍把自己当作世外之人,而不愿拘泥于礼教的束缚,这其实是他为自己塑造的理想人格,为维护这种理想人格的尊严,阮籍便以“青白眼”( [1] , P. 202)来对待周围的人:对于同道中人,他用“青”眼热情相视,而对于礼法之士,则以“白眼”相加。
礼法之士伏义曾如此描述阮籍:“吾闻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抚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张,动与世乖,抗风立侯,蔑若无人。”( [6] , P. 74)阮籍则回答他“弘修渊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灵变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 [6] , P. 68)小人之见能有几何。礼法之士哪能洞察阮籍对理想人格的执着!所以阮籍对礼法之士的蔑视表现了他对于生命境界的追求,而这种不懈的追求恰恰是其生命意识的流露。
4. 结语
阮籍的“放达”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开启了魏晋士人的“放达”之风,使“放达”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显著意象。但阮籍的“放达”在以名教治天下的社会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何曾就多次谏言应该将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正是如此阮籍因“放达”而历来被追究为风教凌迟的罪魁祸首。
阮籍“放达”的局限性是在思想上把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理解成一个混沌的整体,从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来是一种谬误,所以阮籍“放达”的指导思想和行为之间常常存在着他无法超脱又不甘沉沦的悖论:他思想上漠然于是非,行动上却又以“青白眼”加以评判;他试图理解善与恶的统一性,却在行动上极力向善背恶;他想通达生死,却忍不住对生的眷恋和对死的哀伤,故阮籍的精神常常处于一种痛苦挣扎的状态,对于这一点阮籍内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制止儿子效仿自己的“放达”,也许他只希望自己的儿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吧。
总之,阮籍的“放达”是特殊时期的特色产物。我们现代人对阮籍的“放达”应多一些同情和理解,而不能再一味地加以斥责和贬低。毕竟阮籍的“放达”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人世的超脱与弃绝,不论他是如何地放旷不羁,任诞张狂,纵情背礼,傲视群俗等等都是对于他自身焦灼而尴尬生存状态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自我解脱与自我拯救。此外阮籍的“放达”中还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后世文人士子开辟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并不断于尘世的喧嚣之中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这一点永远值得我们去细细体味。
文章引用
郭培玉. 解析阮籍的“放达”
Analysis of Ruan Ji’s “Open Mind”[J].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06(04): 135-14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8.64020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3. 阮籍, 著. 阮步兵咏怀诗注[M]. 黄节, 注. 华忱之, 校订.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4. 谭绍鹏, 甘安顿.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争鸣大观[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 5. 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6. 陈伯君. 阮籍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