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
08
No.
01
(
2020
), Article ID:
34967
,
8
pages
10.12677/OJHS.2020.81001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Zhaohui Bu, Xiangbo W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 19th, 2020; accepted: Apr. 3rd, 2020; published: Apr. 10th, 2020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mission to Tang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Most of them are relatively macroscopic and generalized. They rarely conduc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n a certain mission.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was a rather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one, including the second time Kibino Makibi (きびのまきび) to Tang, the delegation’s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Silla on the New Year’s Day Chaohe, Jianzhen went to Japan successfully, and Abeno Nakamaro (あべ の なかまろ) went back to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events of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By the 11th Mission to Tang, Japan had improve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Northeast Asia, consolidated the rule of the Emperor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both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a mutual social interac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can know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mission. Ambassador Fujiwara Kiyoshi who served as secretary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promoted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Tang. At the same time, as a talent introduction like sending Jianzhen to Japan and the talent Abeno Nakamaro’s (あべ の なかまろ) returning also have a reference to the tal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oday.
Keywords: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Contention of Rank, Jianzhen Cross the Ocean to Japan, Kibino Makibi,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mpact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
——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卜朝晖,吴祥博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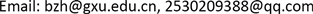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0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10日

摘 要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大多是较为宏观、概述性的论著,很少对某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究。第十一次 [1] 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期间发生了吉备真备二度遣唐、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事件。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主要事件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派遣,提高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巩固了天皇贵族统治、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基于文化传播理论可考察到该使节团的政治、社会影响。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担任秘书监促进了唐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人才引进的鉴真东渡、人才回流的阿倍仲麻吕归国对现今我国的人才策略及发展也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位次之争,鉴真东渡,吉备真备,文化传播理论,影响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于752年末抵唐,大使是藤原清河,副使是大伴古麻吕和第二次遣唐的吉备真备。此次遣唐使团在历次中颇显特别,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753年正月初一朝贺时,日本使团曾与新罗发生位次之争,玄宗皇帝曾“勅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 [2],最终日本使团座次位于新罗使之上;753年归日时,鉴真和尚随使团成功渡日。鉴真自743年开始东渡以来,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最终乘坐此次遣唐使团的第二艘船于同年底抵达日本;滞唐36年之久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在该使团准备动身回国时请求一同归国获准;使团归国途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因所乘坐的船只不幸遭遇风浪未能成功归国,之后大使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吕都终身仕唐未归。因此,此次遣唐使团与历次遣唐使团相比是较为特殊、且遣唐意义重大的一次。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经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先行研究中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几乎没有。关于遣唐使的代表性的论著有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0)、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出版社, 1985)、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等。这些论著都是较为宏观、概述的,主要是从规模、航线、目的、遣唐使次数等宏观角度对遣唐使进行研究,并未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所以本文将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并基于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鉴真东渡事件、阿倍仲麻吕归国事件等历史事件。先行研究中对鉴真东渡、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的研究颇多。如安藤更生的《鉴真在日本》(陈正奇(译), 唐都学刊, 2008.11)、徐永红的《鉴真东渡及对日贡献》(山东大学, 2011.03)等,但先行研究中关于鉴真东渡的研究很少从政治角度,大多从佛教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关于阿倍仲麻吕的研究如今枝二郎的《唐代文化之考察1——阿倍仲麻吕研究》(高文堂(出版), 1979)、卜朝晖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等,主要从他在唐的事迹和与唐朝诗人王维、李白等的交往情况进行研究,很少探究阿倍仲麻吕归国与第十一次遣唐使节团之间的关联。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也很多,如宫田俊彦的《吉备真备》(吉川弘文馆, 1961)、刘明翰的《论吉备真备》(文学史, 1997)等,但是主要考察了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为日本发展所做贡献,及第二次遣唐归国后平叛藤原仲麻吕为日本国家安定所做贡献,几乎并未考察吉备真备第二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所以,本文将从日本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鉴真成功渡日(从政治角度)、阿倍仲麻吕归国原因探究、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对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使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同时,基于文化传播理论,从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2.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唐的重大事件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使节团。其遣唐期间发生了数个对中日交流影响较大的事件。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本节将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察分析。
2.1. 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在753年正月一日朝贡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据《大日本史卷一百一十六列传43大伴古麻吕》中记载“六年(754年),歸自唐,奏曰:「天寶十二載元會,唐主居含元殿,受賀。是日,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臣爭曰:『新羅朝貢于日本久矣,而今反列東畔上,義所不當。』於是,其將軍吳懷實見臣顏色,即引新羅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國上」”。大意是:“副使大伴古麻吕遣唐归国后曾向天皇上奏说:‘天宝十二年(753年)元日朝贡时,唐玄宗在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时,日本使团座次位于吐蕃之下西侧第二位,新罗使团位列大食国之上东侧第一位。大伴古麻吕争议曰:新罗朝贡于日本已经很久了,现在反而位列(日本之上)东侧第一位,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吴怀宝将军引导新罗使至吐蕃下位,引日本使团至大食国上位。”思托《延历僧录》卷二《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中也有记载日本使团与新罗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 [2]。笔者认为此次日本使团与新罗使团的位次之争,日本座次位于新罗之上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非沈仁安在“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研究, 1994-09, pp. 81-84)中论述的“席次的变换丝毫也不改变以藩望高下排定和藩国等位。也得不出在以唐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格局中,日本的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结论”。
唐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作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说是藩属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唐朝时期更甚,据《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著, 1999, 中华书局)记载唐朝时期有“五礼”,其中第二礼“宾礼”就是“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 [3],即(接待)外国使臣来唐时所要遵从的礼节。另外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 [3]。所以这些藩属国在朝贺时的座次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是由鸿胪寺按照藩属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或者与唐的亲疏关系进行座次安排。根据《大日本史卷一百一十六列传43大伴古麻吕》中的记载,最初鸿胪寺给日本安排的座次是“西畔第二吐蕃下”,当时朝贡座次以西为尊。所以,由此可知(在唐看来)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并不太高,是位于新罗、大食国、吐蕃之下的。在此之前的历次遣唐使中,日本使团并未与他国发生位次之争。是因为鸿胪寺对前几次的遣唐使座次安排比较靠前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并且笔者认为在此之前的历次日本遣唐的朝贡座次都不会高于此次的位次。629~661年第一期遣唐使团 [4] 可以说是遣隋使的延续,遣唐使团规模较小,并且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并不发达。虽然在654年进行了“大化革新”,但律法等并不完善还没有进入律令制社会,而且与新罗、吐蕃等与唐朝陆路相邻、往来频繁的藩属国相比与唐关系并不亲密,所以此时期日本使团在当时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太大,因此第一期的日本遣唐使团的座次不会太高。662~697年第二期遣唐使团,主要是基于百济问题和修复唐日关系而派遣的。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了一次水战即白村江之战,最终唐朝、新罗联军取得战争胜利。这一时期,唐日可以说是敌对状态,那么此期间的日本遣唐使团朝贡座次也必不如与唐是盟友关系的新罗。697~758第三期,除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日本共派遣3次遣唐使团,分别是702年、717年、733年,此期间正处于盛唐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规模也较大,是日本遣唐使团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唐日关系友好,唐朝当局曾让赵玄默教授日本使者经学(四书五经),且阿倍仲麻吕在唐滞留多年,也颇得玄宗皇帝赏识。所以此期间日本使团朝贡位次若是高于新罗、吐蕃等的话,那么753年日本使团朝贡时也应在新罗、吐蕃等之上,因为此期间并未发生不利于唐日关系的事件。此外新罗、吐蕃等国与唐关系是明确的藩属国关系,每年会向唐朝缴纳贡品,而日本方面并不认为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国,而是奉行日本自圣德太子时确立的“独立、对等”的外交方针。所以日本在朝贡品上想必也是不如新罗、吐蕃等国的。所以在唐看来,日本的朝贺位次是不如新罗、吐蕃的。那么为什么此次遣唐发生了位次之争呢?笔者认为日本因为遣唐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好地发展,718年《养老律令》完成,日本正式进入律令制国家。历法(大衍历法)、文化(怀风藻完成)等各方面也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地发展。另外白村江之战,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战役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唐日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稳定形成。因此日本使团,不满屈居“西畔第二吐蕃下”的位次安排、并因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罗使团进行位次交换,以期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笔者认为此次日本使团与新罗使团的位次之争,日本座次位于新罗之上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第十一次日本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反映出,此次遣唐使团使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扩大本国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此次遣唐目的与历次遣唐使团使唐目的有很大不同的一点。
2.2. 鉴真东渡事件
鉴真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僧人,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自唐天宝(743年)应日本学问僧荣叡、普照的请求发愿前往日本传戒、弘扬佛法以来,十年之内五次泛海东渡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最终在753年乘坐第十一次遣唐使的第二艘船于同年末抵达日本。但是鉴真第六次成功渡日可以说是偷渡到日本的,因为并未得到当时玄宗皇帝的许可。《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 2000, 中华书局, p. 83)曾有这样的记载:“弟子等先録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另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 [5]。大意为“我们曾上奏皇上,邀请大和尚等去日本传教的事情,不过皇上却命道士前去日本,但日本君王并不崇尚道法,便向皇上奏留春桃原等传教道士,因此也未能获奏大和尚东渡传教”。另外《唐大和上东征传》还有这样的记载“(十月)二十三日庚寅,大使處分:大和尚已下分乘副使已下舟。毕后,大使已下共议曰:‘方今广陵郡知觉和尚向日本国,将欲搜舟,若被搜得,为使有殃;由被风漂还,着唐界,不免罪恶。’由是,众僧总下舟,留。”大意是:“在753年十月二十三日,根据大使清河的安排,鉴真大和尚及渡日的僧人分乘副使的船只渡日。之后,清河与其他遣唐使们商议:现在广陵郡方面已经知晓了鉴真大和尚们要去日本,将会搜船。如果鉴真大和尚们在我们穿被搜查到,恐怕会有灾祸。另外,若不幸遭遇风浪漂还回唐朝境内的话,也会被降罪。所以这一次,登船的渡日僧人全部下船,暂留于唐”。由此可以看出鉴真此次东渡日本可以说是偷渡日本,因为并未得到唐朝当局的许可。
不过日本使团在“若被搜得,为使有殃;由被风漂还,着唐界,不免罪恶”的情况下也曾力邀鉴真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大使藤原清河等去延光寺拜谒鉴真并说“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这是因为日本当时佛教发展及当权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在那个时期日本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课税严重,人民不堪其重,不过寺院有免赋免课的特权,因此有些人就自戒私戒为僧,造成佛门人员混杂,不利于佛教发展。另外,也有一些人投靠寺院成为僧祗户以逃避赋税,随着寺院僧籍奴隶主的势力扩大,执政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贵族阶层想掌握僧籍使僧人为自己服务以巩固自身统治。因此日本效仿唐朝规定:“非经三师七登,不能成为入道,不能取得僧籍”。但当时日本几乎没有能够进行受戒的高僧人数,733年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出使唐朝的普照、荣睿虽聘请到了道璿,但由于道璿威望不高不能进行受戒。所以日本亟需像鉴真一样的高僧前去弘扬佛法,协助日本寺院规范僧籍促进佛教发展;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想通过鉴真掌握僧籍以巩固统治。由此也能推断出此次遣唐使的另一目的就是聘请唐朝高僧,以促进日本佛教发展及借助唐朝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日本的这一举措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人才引进,这对目前中日两国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2.3. 阿倍仲麻吕归国事件
著名的留唐学生阿倍仲麻吕滞唐36年之久,在753年随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归国(后因遭遇风暴未能到达日本)。可以推测此次遣唐使团的遣唐目的之一应是迎接阿倍仲麻吕归国。因为日本需要阿倍仲麻吕这样的汉学人才,希望人才回流。遣唐或者遣隋人员回流政策在推古天皇时期已经有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年),遣隋使惠日等搭载新罗使船归日并向推古天皇上奏说“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業。応喚” [6],所以人才回流也是之后历次遣唐使的遣唐目的之一。据《大日本史》记载“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真備、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 [7],由此也能看出日本对阿倍仲麻吕的重视。当时的日本唐风文化盛行,而在大学寮执教的吉备真备由于政治倾轧又被调离奈良,日本也亟需优秀的汉学人才教授传播唐文化。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归国后,在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任大学助,在大学寮执教。《史记》、《汉书》、《后汉书》在日本的讲授,就始于吉备真备,吉备真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吉备真备调离奈良,日本朝廷也需要一个与吉备真备旗鼓相当的汉学人才来填补空缺,而“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峰聳峻,學海揚漪” [7] 的阿倍仲麻吕无疑是日本朝廷所需的极佳人选。所以,由此可推断出迎接阿倍仲麻吕归国也是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目的之一。
3. 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目的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副使吉备真备是第二次遣唐,这在遣唐使中是很少见的,中日学界关于吉备真备的研究也很多,如宫田俊彦《吉备真备》、刘明翰的《论吉备真备》等。但是主要考察了吉备真备第一次遣唐为日本发展所做贡献,及第二次遣唐归国后平叛藤原仲麻吕为日本国家安定所做贡献,几乎并未考察吉备真备第二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所以本节将对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原因及目的进行考察分析。
吉备真备(695~775年),原名下道真备,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下道氏是吉备地区有力的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出生于备中国下道郡(今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奈良时代(710~794年)的学者、政治家,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著有《私教类聚》50卷。716年(日灵龟二年) 22岁时被选拔为赴唐留学生,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团初次使唐,在唐17年曾拜中国的四门馆助教赵玄默为授业师。734年归国时带回大量书籍书籍、文物等。据据《续日本纪》中正式记载为:“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8]。日本朝廷曾根据《唐礼》进行了礼仪改革,《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和测影铁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吉备真备的第一次遣唐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天文历法、文化艺术的发展。735年被晋升为正六位下并被委担任大学助,738年任东宫皇太子师,为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女帝)讲授《礼记》、《汉书》等,颇受孝谦的赏识和恩宠。后在孝谦天皇“即位於大極殿。吉備朝臣真備並従四位上” [8]、750年“左降従四位上吉備朝臣真備為筑前守” [8]、“俄遷肥前守” [7],后于751年请愿出任遣唐使“以従四位上吉備朝臣真備為入唐副使” [8]。
吉备真备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冒着生命危险再次遣唐的原因,笔者认为吉备真备想改变左迁、不被重用的现状,通过遣唐重回孝谦天皇身边、以期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遣唐使归来之后一般都会升迁得到重用(二是制衡藤原清河或者藤原仲麻吕)。740年藤原仲麻吕在帮助平定藤原广嗣之乱后颇得藤原太后(光明皇后)的信任而很有权势。749年秋七月孝谦天皇即位于大极殿后,藤原仲麻吕晋升为大纳言,兼任紫微令、中卫大将,并在光明皇后和孝谦天皇信任的背景下,掌握了日本朝廷的军政大权。750年,与藤原仲麻吕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吉备真备被贬职为筑前守,并且之后又被贬职为肥前守,远离政治中心。同年日本朝廷筹备遣唐事宜,天平胜宝2年(750年)九月任藤原清河为遣唐大使,副使为大伴古麻吕。之后吉备真备上书请愿出使唐朝。在当时航海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远渡重洋的遣唐途中是较为危险的,也因此每次遣唐之前日本朝廷都会去神社为遣唐使们举行祭祀、祈福活动。而吉备真备甘愿冒着极大地风险也要再次遣唐,说明他急切的希望通过遣唐改变自己目前不被重用的现状。而吉备真备通过再次遣唐也成功地改变左迁的现状,再次遣唐归朝后“進正四位下,陞太宰大貳”。吉备真备再次遣唐同时也不忘汉籍东传,此次回朝曾带回去“唐本灵像”(孔子、颜回等),《东观汉记》。
4. 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下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文化传播理论是文化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与文化进化论相对立,肯定了“传播”的重要性,“传播”是文化学派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文化传播学者用“传播”研究各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相似特性,说明一种文化特质或文化丛(文化元素)如何从一个地方散播到另一个地方的,是文化向外传递、扩散而超出产生地区的一种流动现象 [9]。文化传播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文化圈”学派的格雷布纳(1877~1934) (著的《民族学方法论》认为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分布在什么地方,都宣布它们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英国传播学派的里弗斯(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强调了传播的重要作用)、史密斯(文明一经创造后就只是不断的传播,不可能再有同样的创造)和佩里(任何文化的提高都不能靠自身独立发展,只能通过吸收高级文化传播而来的东西)、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1858~1942) (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每种文化怎样根植于社会集团独一无二的历史以及怎样受外部文化传播的影响)。虽然各文化传播学派过于突出“传播”的重要性甚至观点比较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传播”对一些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有巨大影响。比如唐朝文化通过遣唐使、赴日唐人等对日本奈良文化(或日本文化)的影响。文化传播还具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负面作用 [9]。其中社会功能包含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指文化环境如特质、模式风格诸现象量的渐变和结构性质变,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政治功能是指政治权利对舆论的控制通常通过文化传播进行 [9]。本节笔者将根据文化传播理论,从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4.1. 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体现及其影响
文化传播具有政治功能,文化传播的政治功能是指政治权利对舆论的控制通常通过文化传播进行。并且“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当权统治者)都特别重视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争取民众支持,夺取政权” [9],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时期更是如此,统治者通过控制文化传播掌控舆论,贯彻统治意图巩固自身统治。鉴真东渡之前,日本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课税严重,人民不堪其重,不过寺院有免赋免课的特权,因此有些人就自戒私戒为僧,或投靠寺院成为僧祗户以逃避赋税,随着寺院僧籍奴隶主的势力扩大,执政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贵族统治者亟需一位佛教中的权威僧人协助整顿佛门混乱的状态,帮助贵族阶层掌握僧籍使僧人为自己服务以巩固自身统治。所以鉴真东渡后受到了日本统治者的极大欢迎,曾被大纳言藤原仲麻吕等百余名官员拜访,754年4月为孝谦天皇、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授大乘菩萨戒。被日本统治者极力推崇。之后鉴真为日本僧人传道受戒,协助寺院整治规范了僧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矛盾,巩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而吉备真备通过再次遣唐成功地改变左迁的现状,虽然并未回到政治中心奈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身受到的政治倾轧。之后在九州太宰府励精图治,为以后平定藤原仲麻吕之乱、推行司法改革及删定律令等打下基础。外交方面,753年朝贡仪式上与新罗使团进行的位次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第11次遣唐使团在753年元日朝贡仪式上不满唐朝安排的“位于吐蕃之下西侧第二位”的座次安排,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 [2],证明了白江村战役之后日本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已然变化,形成了唐日新三足鼎立的局势,唐朝已不能忽视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所以此次与新罗的位次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获得唐朝的重视,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4.2. 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体现及其影响
文化传播具有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包含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文化环境如特质、模式、风格诸现象量的渐变和结构性质变,文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吴格言《文化传播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 p. 42)。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变迁。鉴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日本开创了律宗。东渡时带去的大量佛教图书典籍,为日本两大佛教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据《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 中华书局, 2000)记载鉴真和尚曾带去:“《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經》一部,(中略),玄奘法師《西域記》一本十二卷、終南山宣律師《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法銑律師《尼戒本》一卷及疏二卷,合四十八部”。此外、鉴真东渡日本后也毫无保留的向日本民众传授建筑、雕刻、医药、绘画、书法、文学、语言、印刷等技术,为古代日本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日本社会文明的向前发展。
“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吴格言《文化传播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 p. 17),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文化虽然唐文化占据主动地位对日本文化影响比较大,但是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行为虽有强弱之分,但是日本文化也对中国唐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藤原清河在753年归国失败于755年返回长安后,出仕唐朝,因才华能力出众在肃宗(756~762)、代宗(762~779)两代长期担任秘书监。代宗、肃宗,尊崇儒术,在“安禄山之乱,尺简不存”之时,屡屡下诏购募书籍,诏令秘书阁搜访遗留书,并下令抄写书籍。清河为当时的秘书监,掌管国家经籍图书,所以去民间购募书籍、搜访遗留书籍、抄写书籍,应是清河带领当时的秘书监官员来完成的。清河对书籍的购买、抄录以及管理有一定的经验,因为日本的遣唐使在抵唐后,“所得锡赉,尽市文籍”,并且他们也会抄录唐朝典籍带回日本,而身为遣唐大使的藤原清河此次遣唐也不例外。所以清河能更好的复兴图书事业,为“开成(836~840年)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清河在任秘书监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图书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5. 结语
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考察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政治功能方面:鉴真为日本僧人传道受戒,协助寺院整治规范了僧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矛盾,巩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促进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吉备真备再次遣唐的目的是想改变左迁、不被重用的现状,通过遣唐重回孝谦天皇身边、以期实现自己的抱负,并为以后吉备真备进行政治改革打下基础。外交方面,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提高了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与新罗的位次之争的结果是唐玄宗“敕命日本使可与新罗之上” [2],证明了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已然变化,形成了唐日新三足鼎立。而此次位次之争也实现了日本遣唐的目的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社会功能(文化变迁)方面:鉴真成功东渡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技、医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鉴真东渡带去大量佛教典籍,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兴盛。并且鉴真东渡的影响延续之今,依然是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对现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有促进作用。“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也促进了唐朝文化的发展。大使藤原清河归国失败后在任秘书监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图书事业的复兴与发展,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真东渡可以说是日本的人才引进;阿倍仲麻吕归国(虽未成功)可以说是人才回流。当下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对现在我国的人才发展策略具有参考意义。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或遣唐使的文化传播类型是组织传播,日本遣唐使团虽是外交使节,但实际上是按照律令制下的官府规模组建的一套有专职的政府机构。在渴望学习唐先进的政治文化的人文环境下,主动传播吸收唐文化,所以唐文化在日本的受容比较高并且影响深远。这对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具有参考意义,推广文化时应考虑到传播环境和受众的接受度,这样才便于更好的传播中华文化。
文章引用
卜朝晖,吴祥博.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The 11th Mission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J]. 历史学研究, 2020, 08(01): 1-8.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0.81001
参考文献
- 1. 王勇. 日本文化——模仿与创造新轨迹[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92-198.
- 2. 思讬. 延历僧录. 卷二. 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M].
- 3.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 木宫泰彦. 中日文化交流史[M]. 胡锡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5. 真人开元. 唐大和上东征传[M]. 汪向荣,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83.
- 6. 舍人亲王, 等. 日本书纪. 后篇. 卷22. 推古天皇31年7月条.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M].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86: 161.
- 7. 德川光国. 大日本史[M]. 吉川: 吉川弘文馆, 1900.
- 8. 青木夫, 等, 校注. 续日本纪.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3[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0.
- 9. 吴格言. 文化传播学[M].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