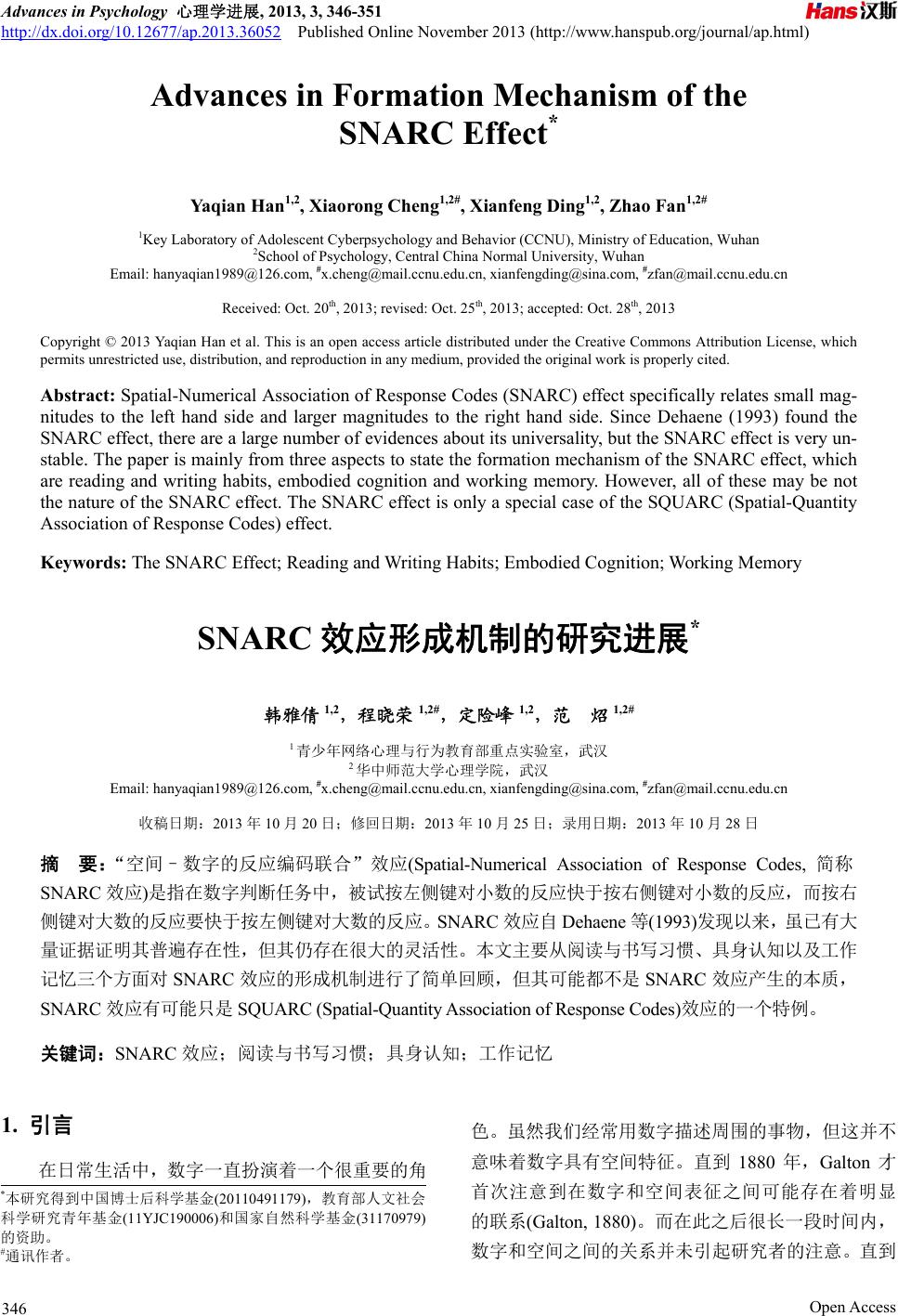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3, 3, 346-351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3.3605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3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html) Advances i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NARC Effect* Yaqian Han1,2, Xiaorong Ch eng1,2#, Xian fe ng Ding1,2, Zhao Fan1,2# 1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2School of Psychology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 n Email: hany a q i a n 1 9 8 9 @126.com, #x.cheng@mail.ccnu .edu.cn, xianfengding@sina.com, #zfan@mail.ccnu.edu.cn Received: Oct. 20th, 2013; revised: Oct. 25th, 2013; accepted: Oct. 28th, 2013 Copyright © 2013 Yaqian Han et a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 ribution, and re 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 d. Abstract: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SNARC) effect specifically relates small mag- nitudes to the left hand side and larger magnitudes to the right hand side. Since Dehaene (1993) found the SNARC effe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vidences about its un iversality, bu t the SNARC effect is very un- stable. The paper is 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 to st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NARC effect, which are reading and writing habits, embodied cognition and working memory. However, all of these may be not the nature of the SNARC effect. The SNARC effect is only a special case of the SQUARC (Spatial-Quantity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 Keywords: The SNARC Effect; Reading and Writing Habits; Embodied Cognition; Working Memory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韩雅倩 1,2,程晓荣 1,2#,定险峰 1,2,范 炤1,2# 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2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Email: hany a q i a n 1 9 8 9 @126.com, #x.cheng@mail.ccnu .edu.cn, xianfengding@sina.com, #zfan@mail.ccnu.edu.cn 收稿日期:2013 年10 月20 日;修回日期:2013 年10 月25 日;录用日期:2013 年10 月28 日 摘 要:“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简称 SNARC 效应)是指在数字判断任务中,被试按左侧键对小数的反应快于按右侧键对小数的反应,而按右 侧键对大数的反应要快于按左侧键对大数的反应。SNARC 效应自 Dehaene 等(1993)发现以来,虽已有大 量证据证明其普遍存在性,但其仍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本文主要从阅读与书写习惯、具身认知以及工作 记忆三个方面对 SNARC 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简单回顾,但其可能都不是 SNARC 效应产生的本质, SNARC 效应有可能只是 SQUARC (Spatial-Quantity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效应的一个特例。 关键词:SNARC 效应;阅读与书写习惯;具身认知;工作记忆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数字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 色。虽然我们经常用数字描述周围的事物,但这并不 意味着数字具有空间特征。直到 1880 年,Galton 才 首次注意到在数字和空间表征之间可能存在着明显 的联系(Galton, 1880)。而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数字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 *本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10491179),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1YJC19000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170979) 的资助。 #通讯作者。 Open Access 346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1990 年,Dehaene 等人才再次发现了数字和空间之间 存在着隐秘的联系(Dehaene, Dupoux, & Mehler, 1990)。此后,Dehaene 等人(1993)采用数字奇偶判断 任务发现,无论数字是奇数还是偶数,按左侧键对小 数的反应总是快于对大数的反应,而相反,按右侧键 对大数的反应总是要快于对小数的反应。因此他们认 为,虽然数字的奇偶判断和数量信息无关,但数量的 空间表征仍被自动激活。Dehaene 等揭示了数字大小 与两侧手反应速度的关系,并且把这种效应命名为 “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简称 SNARC 效应 (Dehaene, Bossini, & Giraux, 1993)。自该效应被发现 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许多针对该 效应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大量研究表明 SNARC 效应 广泛存在,但同时数字的这种空间特性还具有相当的 灵活性(Gevers & Lammertyn, 2005; Wood, Willmes, Nuerk, & Fischer, 2008)。本文旨在简单探讨导致 SNARC 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 2. 阅读与书写习惯的影响 对于 SNARC 效应的获得以及心理数字线的存 在,有“先天”和“后天”两种基本假说。但总体看 来,支持“后天”假说的研究结果占了绝大多数。而 在影响 SNARC效应的后天诸多因素中,许多研究者 都认为阅读与书写习惯对 SNARC效应以及心理数字 线的影响较大。Dehaene 等(1993,实验7)发现,移民 到法国的伊拉克被试,其 SNARC效应强度与他们的 移民时间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伊拉克被 试的读写习惯是从右到左,而法语文本则是从左到右 进行印刷的,因此,随着被试移民的时间越长,他们 表现出的标准 SNARC 效应也就越强。Zebian 以阿拉 伯被试和会阿拉伯语、英语两种语言的阿拉伯被试进 行对比研究,发现习惯与从右到左的阿拉伯读者,表 现出反转的 SNARC 效应,即对小数字右手反应快于 左手,而对大数字左手反应快于右手。而对于那些以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阿拉伯被试来说,反转的 SNARC 效应则明显减弱(Zebian, 2005)。Shaki 和 Fischer (2008)发现,当被试在阅读完一篇俄文文章(从 左到右)或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从右到左)后完成类别 判断任务:其中,在阅读了俄文文章之后,会双语的 俄国–希伯来被试表现出标准的SNARC效应;而在 阅读完希伯来文文章之后,SNARC 效应明显减弱 (Shaki & Fischer, 2008)。台湾学者Yi-hui Hung等人以 阿拉伯数字、繁体汉字、简体汉字为实验材料对台湾 人进行研究发现:台湾人同时存在水平和垂直的心理 数字线。具体表现在:台湾人对阿拉伯数字的表征存 在水平方向的心理数字线,对简体汉字的表征存在垂 直方向的心理数字线,而对繁体汉字不存在任何方向 的心理数字线(Hung, Hung, Tzeng, & Wu, 2008)。他们 认为,之所以简体汉字会出现垂直方向的 SNARC 效 应,是由于在台湾有60%的文本是按照垂直方向印刷 的,而阿拉伯数字几乎不会出现在垂直文本中,繁体 汉字的使用频率太少。此外,Shaki 等人发现文字和 数字的阅读方向均影响 SNARC效应(Shaki, Fischer, & Petrusic, 2009)。在他们的研究中,以色列被试阅读希 伯来文字时是从右向左的,但阅读阿拉伯数字时则是 从左向右的,结果在以色列被试中未发现 SNARC 效 应。以上研究证明了 SNARC 效应本身是一种方向性 效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天学习和读写习惯的影 响。 但是,综合近期的研究,Fischer 和Brugger 认为 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证据表明:阅读与书写习惯不能完 全解释多数的 SNARC 效应,不可能成为 SNARC 效 应最终的原因(Fischer & Brugger, 2011)。第一,即使 在一个给定的文化中,一个定义良好的单向的阅读方 向的概念也太过简单化。例如希伯来语读者,他们通 常是从右向左的阅读文本,但是对于镶嵌在其中的数 字,他们则从左向右阅读。因此,在希伯来被试中并 未出现 SNARC效应,其原因推测起来可能是因为文 字和数字的阅读习惯互相抵消了(Shaki, et al., 2009)。 与此观察相一致,对于希伯来被试来说,当数字与空 间的联合方式与一般的阅读方向相一致时(Fischer, Mills, & Shaki, 2010),或者被试的反应方式和数字与 空间的联合方式相冲突时,例如用垂直的键进行反应 (Shaki & Fischer, 2012),便会出现标准的 SNARC 效 应。Hung 等人 (2008)在中国被试中发现的垂直方向上 的SNARC 效应,同样暗示 SNARC 效应的多维性。 而日本学者Ito 和Hatta 以日本被试为研究对象,在垂 直方向上发现了反转的SNARC效应(即大数位于数字 线的上方而小数位于数字线的下方),他们的心理数字 Open Access 347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线与日本被试的读写习惯正好相反。第二,暴露在一 种文化中的时间逐渐形成一个人的SNARC效应的假 设与最近的研究发现相违背。俄语–希伯来语双语被 试在阅读几分钟俄语或者希伯来语文字之后,便会改 变他们 SNARC 效应的方向(Shaki & Fischer, 2008), 事实上,仅仅只阅读一个俄语单词或者希伯来语单词 便能改变 SNARC 效应的大小(Fisch er, Shaki, & Cruise, 2009)。甚至在阅读过程中,SNARC效应也依赖于数 字在文章中的位置(Fischer, et al., 2010)。这些研究清 楚地表明,阅读习惯的作用比之前认为的要更加短 暂。第三,发展心理学的数据为反对阅读作为SNARC 效应起源的角色提供了证据。例如,4、5岁的儿童在 按照升序从左向右数数时,他们已经能够很好的探索 物体(Opfer & Furlong, 2011)。第四,在完全不存在阅 读习惯的情况下,SNARC效应仍可以出现,有关动 物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Rugani, Kelly, Szelest, Regolin, & Vallortigara, 2010; Rugani, Vallorti- gara, Vallini, & Regolin, 2011)。 总之,即使阅读与书写习惯对SNARC效应有影 响,那么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成为解释 SNARC 效应的主要原因。 3. 具身认知的解释 考虑到用阅读与书写习惯解释SNARC效应起源 的有限性,Fischer 等人开始用具有普遍性和跨文化变 异性的方向性习惯——手指计数来解释 SNARC 效应 的起源(Fischer & Brugger, 2011)。世界各地,大部分 小孩最初都是通过手指计数来获得数的概念的,手指 计数拥有很长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但 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个体用手指计数的方式是不同 的。Lindemann 等人通过一个在线调查发现:在手指 计数策略中,中东地区被试和西方被试存在文化差 异,即许多西方被试(如美国人)倾向于从左手开始计 数,而且将1与他们的大拇指联合在一起;而大部分 中东被试(如伊朗人)更喜欢从右手开始计数,并将1 与他们的小拇指联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一偏差可 能与眼睛扫描习惯而非阅读书写习惯有关(Lindemann, Alipour, & Fischer, 2011)。Fischer (2008)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苏格兰被试中有 2/3 的成年人是从左手的大拇 指开始计数的,且这一发现与他们是左利手或右利手 无关。然后分别挑选从左手开始和从右手开始的计数 的被试完成奇偶判断任务,结果发现两类被试表现出 不同的 SNARC效应大小,从左手开始计数的被试有 显著的 SNARC效应,而从右手开始计数的被试中未 发现 SNARC 效应(Fischer, 2008)。Fischer 认为,这一 结果表明手指计数习惯可能是SNARC效应发生的原 因。而 Sato 和Lalain的研究发现与Fischer 的结果相 冲突,法国被试更倾向于从右手开始计数,而且从左 手开始计数或从右手开始计数与他们是左利手或右 利手有一定的联系(Sato & Lalain, 2008)。至于其中的 原因还不清楚,可能与实验方法或特定的文化背景有 关。Riello 和Rusconi 对计数习惯是从大拇指到小拇 指的被试进行单手的数字判断测验。结果发现当右手 的手掌朝下时或者是左手的手掌朝上时,它们分别的 计数方向跟心理数字线是一致的,即从大拇指到小拇 指都是从左往右的。而当右手手掌朝上,左手手掌朝 下时,每只手的计数方向与心理数字线的方向相反, 从大拇指到小拇指是从右往左的。在前一种情况下, 发现了标准的 SNARC 效应,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并没 有发现 SNARC效应。因此,虽然在两只手上都发现 了SNARC 效应,但分别都是只在一种姿势中存在 SNARC 效应(Riello & Rusconi, 2011)。该研究说明了 SNARC 效应不仅与手指计数的方式有关,而且与手 掌的姿势有关。 手指计数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是通过具身认知 来进一步解释的(Fischer, 2012; Fischer & Brugger, 2011; Tschentscher, Hauk, Fischer, & Pulvermüller, 2011)。近几年来,具身认知观已经成为认知心理学研 究的一个新取向,其中心含义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 方式而形成的。根据具身认知观,认知既是具身的, 同时又是嵌入的,大脑嵌入身体,身体也嵌入环境, 这就构成了一体的认知系统(叶浩生,2010)。这里的 “身体”概念不仅指脑或者神经机制等身体的解剖学 结构,而且还包括宏观上的身体构造和状态、身体的 活动方式、身体的物理属性以及身体的特殊感觉—运 动通道等方面。Loetscher 等人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头 保持不动和头向左或向右偏转40˚的条件下,产生 1~30 之间的随机数字。结果发现,当被试头偏向左边 时,产生更多的小数字;而当头偏向右边时,产生更 Open Access 348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多的大数字(Loetscher, Schwarz, Schubiger, & Brugger, 2008)。最近也有研究表明,身体的物理状态会影响数 量的表征(Eerland, Guadalupe, & Zwaan, 2011)。该研究 让被试在不同的身体姿势下估计埃菲尔铁塔的高度, 结果表明,被试身体左倾时比身体正立和右倾时对埃 菲尔铁塔高度的估计明显要小。此外,张丽等人的研 究结果表明,SNARC 效应是否出现受到身体形式的 影响,只有数字的空间特性必须和参与任务的身体表 征相一致时,SNARC 效应才会出现。进一步地,被 试在单独情景下完成 Go/No-go 任务时没有 SNARC 效应出现,而合作情景下则出现SNARC效应,这表 明社会环境对 SNARC 效应也有影响,并进一步为具 身认知观提供了支持(张丽,陈雪梅,王琦&李红, 2012)。 4. 工作记忆的影响 一些研究者认为,数字沿着心理数字线进行空间 表征的过程是自动化的,不需要设置行为目标,也不 需要进行有意识的监控(Ganor-Stern, Tzelgov, & El- lenbogen, 2007)。奇偶判断任务中所表现出的 SNARC 效应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大量支持。Fischer 等人的发现 进一步论证了数字的自动空间编码。Fischer等人(2003) 从空间注意的视角对数字加工引起的空间信息的自 动激活进行了研究,当将数字呈现在屏幕中央时,被 试仅仅是注视数字就会引起空间注意的转移,当呈现 刺激为小数(1 或2)时,左侧刺激的探测要快于右侧; 当呈现刺激为大数(8 或9)时,右侧刺激的探测要快于 左侧(Fischer, Castel, Dodd, & Pratt, 2003)。张宇和游旭 群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对负数的低水平加工也可以引 起空间注意的转移(张宇 & 游旭群, 2012)。 但近来也有大量研究表明,SNARC 效应具有很 强的情境依赖性(Bächtold, Baumüller, & Brugger, 1998; Fischer, et al., 2010),SNARC 效应的发生可能依赖于 有意识的运用实验任务所需要的空间参照框架。 Fischer 最近提出,数字的空间表征可能是个体根据当 前任务的需求所做出的策略性决策,而非心理数字线 自动激活的结果(Fischer, 2006)。而工作记忆作为一种 对信息进行短暂加工和储存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 在许多复杂的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Baddeley提出, 工作记忆并非是个单一系统,而是由多种成分组成, 包括注意控制系统—中枢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 以及为其服务的两个子系统——“负责视觉材料暂时 贮存和处理的视空初步加工系统”和“负责口语材料 暂时存贮和处理的语音回路”(Baddeley, 1992)。目前 已有研究表明,工作记忆也影响着SNARC效应的发 生。 Lindemann等人要求被试在进行奇偶判断任务之 前记忆一个由三个数字构成的序列(数字从左向右排 列,分为升序,如3-4-5;降序,如5-4-3 以及乱序, 如5-3-4),在完成奇偶判断任务之后,回忆屏幕上随 机出现的一个数字在之前记忆序列中的位置。在实验 1中,三种数字记忆序列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实验单元 中,结果只有在降序的条件下,SNARC 效应消失; 而在实验2中,当三种数字记忆序列在每一个试次中 发生变化时,三种条件下均出现标准的 SNARC 效应 (Lindemann, Abolafia, Pratt, & Bekkering, 2008)。 Lindemann等人认为,数字的空间编码是运用认知编 码策略处理数字大小信息的结果,对工作记忆的需求 影响着 SNARC效应的发生。Herrera 等人要求被试在 单一任务或双任务(外加语音负荷或空间负荷)的条件 下完成大小判断任务。在双任务的实验条件下,被试 在进行大小比较任务时,外加了语音的或者空间的工 作记忆任务,而语音的或者空间的信息需要被试进行 记忆,以便在随后的回忆测试中予以检查(Herrera, Macizo, & Semenza, 2008)。结果发现,在双任务–空 间负荷条件下,没有出现 SNARC效应,而在单一任 务和双任务–语音条件下均出现了标准的 SNARC 效 应。Van Dijck等人(2009)进一步推进了 Herrera 等人 的研究,他们在进行奇偶判断任务或大小比较任务 时,均外加了语音或空间工作记忆,结果在工作记忆 类型和实验任务类型中表现出了双重分离。SNARC 效应在奇偶判断任务加语音工作记忆任务和大小比 较任务加空间工作记忆任务中消失(Van Dijck, Gevers, & Fias, 2009)。这些发现首先为反对空间数字联合有 相同的空间编码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此外,它们 表明,数字与不同的空间编码相联合,这依赖于不同 的实验任务类型,有一个视空的和一个语音的调节中 介。Crollen 等人通过对早期失明、后期失明和视力正 常的被试的研究仍表明 SNARC 效应在大小判断任务 中,其起源于视空联合;而在奇偶判断中,起源于语 Open Access 349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音联合(Crollen, Dormal, Seron, Lepore, & Collignon, 2011)。Van Dijck等人(2011)进一步检验了长时记忆和 工作记忆对 SNARC效应的影响。在实验 1中,首先 给被试呈现5个随机数字,要求被试记住这5个数字 及其顺序,然后进行奇偶判断任务,但只对之前记忆 的数字进行反应。如果数字大小与反应出现交互作 用,则支持长时记忆对 SNARC 效应的解释;如果记 忆的顺序与反应出现交互作用,则支持工作记忆对 SNARC 效应的解释;如果三者出现交互作用,则长 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共同解释SNARC效应。实验结果 出现了记忆顺序与反应的显著交互作用,支持工作记 忆的重要性。在实验2中,他们采用水果和蔬菜代替 数字,重复实验 1,将奇偶判断改为水果–蔬菜判断。 结果仍支持工作记忆顺序对SNARC效应的影响(van Dijck & Fias, 2011)。Sallisas采用 Fischer (2003)的实验 范式进行 ERP 研究,结果同样发现了工作记忆对 SNARC 效应的作用(Salillas, El Yagoubi, & Semenza, 2008)。 除了上述研究直接证明 SNARC 效应与工作记忆 的关系之外,以往研究也能很好的被其解释,如负数 在心理数字线上的位置,究竟是按照其数值大小还是 按照其绝对值大小进行表征,取决于负号是否需要参 与到实验任务中,如在大小比较任务中,需要负号的 参与;而在奇偶判断任务中便不需要其参与(高在峰 et al.,2009;Shaki & Petrusic,2005;Tzelgov, Ganor-Stern & Maymon-Schreiber,2009),而这一过程恰好涉及到 工作记忆。Dehaene 等人(1993)和Fias 等人(1996)以及 Baichtold 等人(1998)的实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工作记 忆的原因予以解释。此外,定险峰等人的实验结果也 支持工作记忆对 SNARC 效应的解释,他们以俄文字 母为实验材料,让中国被试先学习水平印刷和垂直印 刷的俄文材料,然后对俄文材料的顺序进行大小判断, 结果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均发现了 SNARC效应(定 险峰,靖桂芳&徐成,2010)。总之,工作记忆能够很 好的解释一些对于SNARC 效应的发现,是影响 SNARC 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 Ficher所言, SNARC 效应可能仅仅是在当前任务中,被试的一种策 略性反应(Fischer, 2006)。 5. 小结与展望 SNARC 效应自发现以来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 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心理数字线”理论一直是 解释 SNARC 效应的经典理论。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 研究结果表明,该理论已经不能很好的解释 SNARC 效应。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或导致了 SNARC 效 应?本文简单回顾了阅读与书写习惯、具身认知以及 工作记忆对 SNARC 效应的解释。前两种观点主要强 调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对SNARC 效应形成的影 响,而后一种观点则认为 SNARC效应的形成是短暂 的,与长时记忆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这三者均能从 不同的方面解释部分的 SNARC 效应,但其可能都不 是SNARC效应产生的本质。 此外,SNARC 效应究竟是特异性的,还是仅仅只 是所有包含数字信息或者顺序信息的刺激与空间位置 关系的一种特例?除了 SNARC 效应之外,最近也有 研究者提出了 STEARC (spatial-tempor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效应,即在人脑中也存在一条类似于心 理数字线的心理时间线,过去/短/早表征在时间线的左 边,而未来/长/晚表征在时间线的右边(顾艳艳&张志 杰,2012;Ishihara Keller,Rossetti & Prinz,2008; Vallesi,McIntosh & Stuss,2011)。而且,跨文化研究 表明,心理时间线的表征方式同样受到读写习惯的影 响(Boroditsky, Fuhrman, & McCormick, 2011; Ouellet, Santiago, Israeli, & Gabay, 2010)。根据 Walsh(2003)提 出的 ATOM理论,时间、空间和数字共享一个数量系 统,那么,SNARC效应和 STEARC 效应以及 SMARC (Spatial-Mus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效应 (Rusconi, Kwan, Giordano, Umilta, & Butterworth, 2006) 在本质上是不是相同的?此外,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 SNARC 效应只是 SQUARC (Spatial-Quantity Associa- tion of Response Codes)效应的一个特例(Kirjakovski & Utsuki, 2012)。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结合行为研究和脑电研 究进一步探索 SNARC 效应的本质,探讨 SNARC 效 应是否是特异存在的以及影响 SNARC 效应的有无、 大小及方向的主要因素,并注重探讨各种因素间的交 互作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定险峰, 靖桂芳, & 徐成 (2010). SNARC 效应起源的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5期, 1258-1261. Open Access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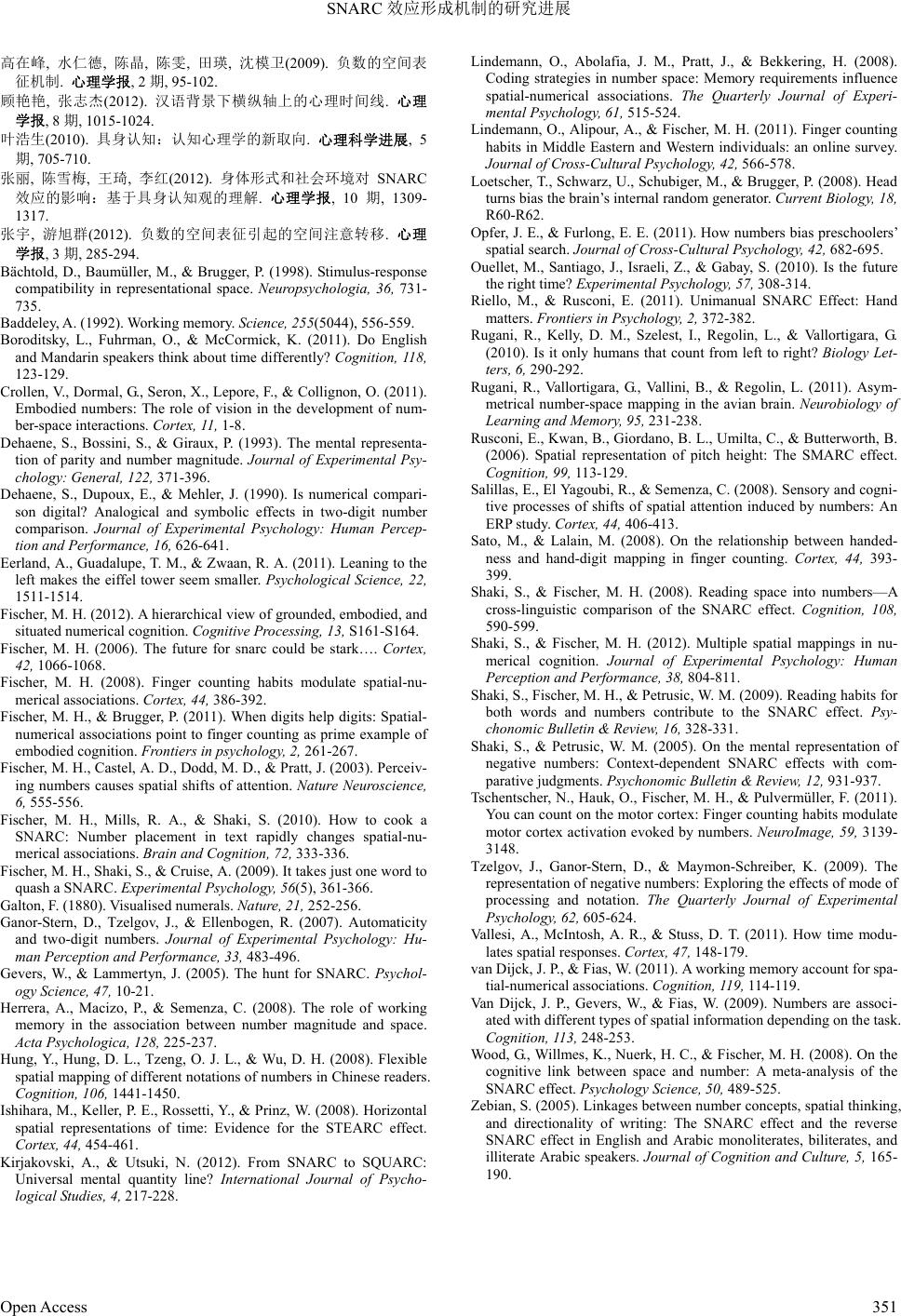 SNARC 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Open Access 351 高在峰, 水仁德, 陈晶, 陈雯, 田瑛, 沈模卫(2009). 负数的空间表 征机制. 心理学报, 2期, 95-102. 顾艳艳, 张志杰(2012). 汉语背景下横纵轴上的心理时间线. 心理 学报, 8期, 1015-1024. 叶浩生(2010). 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 向. 心理科学进展, 5 期, 705-710. 张丽, 陈雪梅, 王琦, 李红(2012). 身体形式和社会环境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基于具身认知观的理解. 心理学报, 10期, 1309- 1317. 张宇, 游旭群(2012). 负数的空间表征引起的空间注意转移. 心理 学报, 3期, 285-294. Bächtold, D., Baumüller, M., & Brugger, P. (1998).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in representational space. Neuropsychologia, 36, 731- 735. Baddeley , A. (1992). W orking memory . Science, 255(5044), 556-559. Boroditsky, L., Fuhrman, O., & McCormick, K. (2011). Do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ers think about time differently? Cognition, 118, 123-129. Crollen, V., Dormal, G., Seron, X., Lepore, F., & Collignon, O. (2011). Embodied numbers: The role of vi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um- ber-space interactions. Cortex, 11, 1-8. Dehaene, S., Bossini, S., & Giraux, P. (1993). The mental representa- tion of parity and number magnitud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 chology: General, 122, 371-396. Dehaene, S., Dupoux, E., & Mehler, J. (1990). Is numerical compari- son digital? Analogical and symbolic effects in two-digit number comparis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 tion and Performance, 16, 626-641. Eerland, A., Guadalupe, T. M., & Zwaan, R. A. (2011). Leaning to the left makes the eiffel tower seem small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1511-1514. Fischer, M. H. (2012). A hierarchical view of grounded, embodied, and situated numerical cognition. Cognitive P rocessing, 13, S161-S164. Fischer, M. H. (2006). The future for snarc could be stark…. Cortex, 42, 1066-1068. Fischer, M. H. (2008). Finger counting habits modulate spatial-nu- merical associations. Cortex, 44, 386-392. Fischer, M. H., & Brugger, P. (2011). When digits help digits: 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s point to finger counting as prime example of embodied cogni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 ogy, 2, 261-267. Fischer, M. H., Castel, A. D., Dodd, M. D., & Pratt, J. (2003). Perceiv- ing numbers causes spatial shifts of attention. Nature Neuroscience, 6, 555-556. Fischer, M. H., Mills, R. A., & Shaki, S. (2010). How to cook a SNARC: Number placement in text rapidly changes spatial-nu- merical associations. Brain and Cognition, 7 2, 333-336. Fischer, M. H., Shaki, S., & Cruise, A. (2009). It takes just one word to quash a SNARC.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6(5), 361-366. Galton, F. (1880). Visualised numerals. Nature, 21, 252-256. Ganor-Stern, D., Tzelgov, J., & Ellenbogen, R. (2007). Automaticity and two-digit numb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 man Perception and Perfo rma nce , 33, 483-496. Gevers, W., & Lammertyn, J. (2005). The hunt for SNARC. Psychol- ogy Science, 47, 10-21. Herrera, A., Macizo, P., & Semenza, C. (2008). 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 magnitude and space. Acta Psychologica, 128, 225-237. Hung, Y., Hung, D. L., Tzeng, O. J. L., & Wu, D. H. (2008). Flexible spatial mapping of different notations of numbers in Chinese readers. Cognition, 106, 1441- 1450. Ishihara, M., Keller, P. E., Rossetti, Y., & Prinz, W. (2008). Horizont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time: Evidence for the STEARC effect. Cortex, 44, 454-461. Kirjakovski, A., & Utsuki, N. (2012). From SNARC to SQUARC: Universal mental quantity 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 logical Studies, 4, 217-228. Lindemann, O., Abolafia, J. M., Pratt, J., & Bekkering, H. (2008). Coding strategies in number space: Memory requirements influence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 mental Psychology, 61, 515-524. Lindemann, O., Alipour, A., & Fischer, M. H. (2011). Finger counting habits in Middle Eastern and Western individuals: an online surve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2, 566-578. Loetscher, T., Schwarz, U., Schubiger, M., & Brugger, P. (2008). Head turns bias the brain’s internal random generator. Current Biology, 18, R60-R62. Opfer, J. E., & Furlong, E. E. (2011). How numbers bias preschoolers’ spatial searc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2, 682-695. Ouellet, M., Santiago, J., Israeli, Z., & Gabay, S. (2010). Is the future the right tim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7, 308-314. Riello, M., & Rusconi, E. (2011). Unimanual SNARC Effect: Hand matters. Fr o nt ier s in Psychology, 2, 372-382. Rugani, R., Kelly, D. M., Szelest, I., Regolin, L., & Vallortigara, G. (2010). Is it only humans that count from left to right? Biology Let- ters, 6, 290-292. Rugani, R., Vallortigara, G., Vallini, B., & Regolin, L. (2011). Asym- metrical number-space mapping in the avian brai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95, 231-238. Rusconi, E., Kwan, B., Giordano, B. L., Umilta, C., & Butterworth, B. (2006).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pitch height: The SMARC effect. Cognition, 99, 113-129. Salillas, E., El Yagoubi, R., & Semenza, C. (2008). Sensory and cogni- tive processes of shifts of spatial attention induced by numbers: An ERP study. Cortex, 44, 406-413. Sato, M., & Lalain, M. (200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ed- ness and hand-digit mapping in finger counting. Cortex, 44, 393- 399. Shaki, S., & Fischer, M. H. (2008). Reading space into numbers—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of the SNARC effect. Cognition, 108, 590-599. Shaki, S., & Fischer, M. H. (2012). Multiple spatial mappings in nu- merical cogn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 ce, 38, 804-811. Shaki, S., Fischer, M. H., & Petrusic, W. M. (2009). Reading habits for both words and numbers contribute to the SNARC effect. Psy- 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6, 328-331. Shaki, S., & Petrusic, W. M. (2005). On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negative numbers: Context-dependent SNARC effects with com- parative judgments.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2, 931-937. Tschentscher, N., Hauk, O., Fischer, M. H., & Pulvermüller, F. (2011). You can count on the motor cortex: Finger counting habits modulate motor cortex activation evoked by numbers. NeuroImage, 59, 3139- 3148. Tzelgov, J., Ganor-Stern, D., & Maymon-Schreiber, K. (2009). The representation of negative numbers: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mode of processing and not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2, 605-624. Vallesi, A., McIntosh, A. R., & Stuss, D. T. (2011). How time modu- lates spatial responses. Cortex, 47, 148-179. van Dijck, J. P., & Fias, W. (2011). A working memory account for spa- 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s. Cognition, 119, 114-119. Van Dijck, J. P., Gevers, W., & Fias, W. (2009). Numbers are associ- at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patial information depending on the task. Cognition, 113, 248-253. Wood, G., Willmes, K., Nuerk, H. C., & Fischer, M. H. (2008). On the cognitive link between space and numb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SNARC effect. P sychology Science, 50, 489-525. Zebian, S. (2005). Linkages between number concepts, spatial thinking, and directionality of writing: The SNARC effect and the reverse SNARC effect in English and Arabic monoliterates, biliterates, and illiterate Arabic speaker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5, 165-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