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09
No.
10
(
2020
), Article ID:
38343
,
10
pages
10.12677/ASS.2020.910226
政策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国之治中的应用
杨溢群,卢笛声
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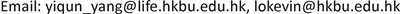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8日;录用日期:2020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8日

摘要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如今成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政策网络理论内涵丰富,兼具宏观微观中观研究视角,显示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点,在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和治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色。在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理论发展、逻辑演进、学派思想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和价值,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但该理论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提供什么借鉴和启发、理论本土化前景如何,有待继续探索。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关键词
政策网络理论,中国之治,政策科学
Policy Network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hinese Governance
Yiqun Yang, Kevin L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Received: Oct. 8th, 2020; accepted: Oct. 21st, 2020; published: Oct. 28th, 2020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developed to three distinct schools: the American school, the British school, and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 school.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become an orthodoxy in western public policy studies.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macro-, meso-, and micro-perspectives, the theory is characterized by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governance mode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scholars have increasingly adopted the theory to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governance. However, what can be learned and inspired from the theory is still to be explored, particularly to Chines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argue that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potential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China; meanwhile, the same applies to China’s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behind it.
Keywords:Policy Network Theory, Chinese Governance, Policy Science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以德国、荷兰为代表)。该理论把公共政策现象重新概念化,在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重要贡献 [1]。它是指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基于资源交换和互赖原则,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建立行动联盟或利益共同体,产生政策网络关系,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执行等环节 [2]。它是政策科学从政策分析范式进入政策研究范式之际出现的新兴理论 [3],是市场和层级形式之外的第三种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具有非层级的(non-hierarchical)、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本质 [4],其共享信息、协调利益、动员资源的功能 [5] 有利于为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提供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之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为节点,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各阶段一脉相承,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 [6]。从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到十九大进入“新时代”,中国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构成了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之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逐步从“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围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从13个方面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明确了制度与治理的关系,即治理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制度及其执行力。全会第一次在制度层面概括总结治国理政的事业和工作,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之治的宏图愿景。
向内看,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中国之治的特色;向外看,全球化使得资本、技术等要素全球流动,国家治理等结构受到影响发生变动 [7],从而让国内的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层 [8],外交顶层设计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中国之治正是在不断加深的“网络化”背景下,在制度体系内展开。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从西方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公共管理研究不断发展壮大 [9] [10]。政策网络理论是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现有国内外文献对其发展脉络、学派思想、逻辑演进、网络类型、网络特征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肯定了理论价值,也指出了理论缺陷,部分文献聚焦中国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做了实证研究。但政策网络理论落地中国时间并不长,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背景下,能为治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什么借鉴与启发,在中国场域中的本土化前景如何,需要进一步探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需要。
2. 政策网络理论的时空谱系
政策网络理论的源头和产生略有复杂,理论发展横跨多国,各学派观点不一但又有同质性,对理论时空演进的把握奠定了后续研究与反思的基础。
2.1. 理论缘起与产生背景
政策网络的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1年,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在《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一书中,用一章内容专门讲述“行政过程的关系网”(the web of relationship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呈现了众多参与者参与到复杂的、非正式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为后来次级系统和次级政府概念的形成作出贡献。
学界认为,从理论渊源看,政策网络理论的源头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学中精英主义(elit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就权力是否平均分配的讨论,提出了次级系统(subsystem)和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等概念,对政策网络概念的产生有启发作用,七十年代,欧洲针对“利益集团的协调”问题,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法团主义1 (corporatism)出现争论,政策网络分析是两个“主义”的替代;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组织社会学中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强调任何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通常都依赖于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三是政策科学的过程理论被认为提供了知识来源;四是复杂性理论被认为是新兴理论来源,特别在政策网络理论分化阶段 [3] [11] [12] [13]。
从产生背景看,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主体之间配合协调、依赖合作关系加强,具体指公民、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逐渐关注公共政策并参与其中,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越来越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执行;二是治理方式由政府统治向协调式发展,政策过程日趋复杂,原有理论无法解释跨层级、跨部门、跨组织、跨主体的复杂网络;三是传统的政策分析视角不足,基于整体主义、聚焦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的宏观研究方法,和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聚焦个人或单个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行为机制的微观研究方法,都无法解释分析某些政策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聚焦政府和利益团体的关系的中观研究视角,在宏观和微观分析之间架起桥梁;四是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中心缺失”(centerless)现象,政策主体结构碎片化、部门化和分权化,政府无法凭一己之力处理公共事务 [14] [15] [16]。
1977年,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最早出现“政策网络”一词,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寻求合作,建立相互依赖关系。
2.2. 学派兴起与理论发展
具体来说,政策网络理论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从微观层面对多个政策主体的互动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概念——次级系统和次级政府 [11]。二战时,格里菲斯(Griffith) [17] 认为,政策是在由社会利益和问题构成的“旋涡”(vortex)中制定,利益攸关人员有能力加入其中干预政策过程,并具有合法性,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崇尚社会扩散和未经协调的团体的多元。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关注,但二战后,促成了“次级系统”(subsystem)概念的产生,用以讨论国会、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在次级单元中,彼此间的关系和互动,揭示了政策网络的本质 [18]。60年代,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 [19] 最早使用“次级政府”(sub-government) (次政府、亚政府)概念描述华盛顿政府的专家、利益代表和政策人员如何组成行动整体,制定政策,解决复杂问题。后来,格兰特·麦克内尔(Grant McConnell) [20] “私营政府”“国家俘获”补充内涵,说明私人利益在次级政府中的主导力量,控制俘获公务人员达成目的。罗威(Lowi)把政府、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构成的稳固的、排他的、可预见的封闭体系比喻为“铁三角”(iron triangle) [21]。70年代,雷普利(Ripley)和富兰克林(Franklin) [22] 发展了次级政府的研究,将之界定为政策的实质性领域内,有效制定大部分常规决策的个人集群,包括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然而,黑克罗(Heclo) [23] 持相反观点,认为决策不是在“铁三角”封闭有限的空间,而是在一种非正式的、开放的、不可预见的“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中进行,参与者无限且复杂。80年代,安德鲁·麦克法兰(Andrew McFarland) [24] 把议题网络看作是,政府机关、生产者或专业利益集团(producer or professional group)和反对性公益团体(opposing public interest group)三者组成的三位一体权力(triadic power),就同一议题出现的三种不同面向的网络关系,政府、议员、专家学者、游说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包含在内,反复沟通。美国学派中,政策网络的类似概念还有政策社区(policy community) [25]、决策网络(decision network) [26]、行动者联盟(advocacy coalition) [27] 等,丰富了政策网络研究。
受美国研究传统中次级政府理论的影响,英国的理查森(Richardson)和乔丹(Jordan)借用政策社区的概念,指出英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在政府和压力集团构成的次级系统中协商运作 [28],目标在于进行“官僚调节”(bureaucratic accommodation) [29],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且认为这个概念是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大部分政策制定过程的关键 [28]。这种研究路径沿袭了美国的政治、政策科学思想,强调美国的理论观念对英国的影响,与之不同的英国学派的另一种路径是以罗茨(Rhodes)、马什(Marsh)为代表的学者,受欧洲组织间关系理论的影响,重视政策网络中政治机构间的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政策网络起源于英国。罗茨不赞同美国的铁三角、次级政府等理论适用英国的观点,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发生在中央和地方因资源依赖而形成的博弈关系的政策网络中,这些资源包括宪法法律资源,也包括组织、财政、政治和信息等资源,这个政策网络是中观概念 [30]。与美国学派概念模糊不同,罗茨详述定义,并根据成员资格、类型和资源分配三个维度,按网络关系近疏排列,把政策网络看作一个包含五种网络类型的连续体,一头是紧密的政策社区,一头是松散的议题网络,中间为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政府间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和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这就是罗茨模型(Rhodes Model) [31],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资源交换(resource-exchange)、博弈互动(rules of the game)和网络自治(significant autonomy)是该模型的四个核心假设,也是政策网络的特征,后经研究的不断深入、争论,罗茨模型被完善为四维度(成员资格、整合程度、资源和权力)两分类(政策社区、议题网络)的网络类型 [13] [30]。罗茨因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集大成者 [14]。
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发生变革,政府角色减弱,私营部门崛起,国家和社会边界模糊,共同参与公共治理过程 [32]。于是,德国学者发现,治理不再是政府对社会的外部控制,而是由多个治理主体促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相互联系,交换信息等资源 [33],政策网络成为一种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的社会结构形式 [34],一种区别于层级制和市场制的专门的治理模式 [1]。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政策网络是两种模式的组合 [35]。德国学派从宏观层面研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强调因为社会的复杂多元,国家和社会组织相互依赖,形成了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政策网络,以弥补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 [36]。从这点上讲,政策网络能够横向地、协商地自我协调,协调出正和结果,使网络行动者都受益,也正是在协商过程中,行动者的密切互动促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提高了问题解决能力,避免了两种传统治理模式出现的问题 [3],因此,网络的实质是层级制的影子(shadow of hierarchy) [37],一方面非国家行动者获得授权,有一定的治理执行力,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可以修正“影子”行动者的不灵。虽然,荷兰学派同样是从宏观角度研究,但荷兰学者重视的是网络治理,即治理成功与否在于网络治理是否有效,包括工具主义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互动视角(interactive perspective)和制度主义视角(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的研究 [38]。90年代,德荷等欧洲大陆学者继续治理途径的研究,开始把政策网络称为治理网络,关注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的关系 [39]。一种是博弈管理(game management),认为应在已有网络的基础上,重视网络行动者良好的行为和彼此间互动的质量,强调网络管理者必须是激励者和协调者;一种是网络建构(network structuring),认为应改变现有网络结构,用新网络达成一致意见,实现治理;两种观点从行动者关系、规则、资源、认知等方面都提出了战略,因此两者内容并不完全割裂,而是互有交叉 [40] [41] [42]。
有学者将这些国家的研究条理化,总结出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研究属于利益调和学派(interest intermediation school),欧洲大陆以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研究属于治理学派(governance school) [4]。此外,政策网络研究还跟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结合,利用量化手段,通过复杂直观的结构图,不同层面的技术分析以及模型建构,实现政策网络分析(policy network analysis) [43] [44] [45]。
2.3. 简要评述
政策网络理论经过五十多年的时空发展(表1),理论内涵不断丰富,研究范围跨越大西洋两岸,形成了多样又独具特色的流派,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同质性。在政治学、组织社会学、政策科学等理论和多种背景影响下,政策网络思想形成,政策网络理论渐露形态。复杂多元的产生背景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了政策网络不同的含义。时至今日,政策网络没有一个确切的、达成共识的定义,不同学者从治理、政策主体或主体关系、资源依赖或国家自主性不同角度出发给予解释 [46]。但在概念演进中,“依赖”“资源交换”“多个行动者”等关键词始终是政策网络理论的支撑。一个最经典的定义诠释,政策网络是“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 [47]。
第二,异质性。就学派而言,美国和英国研究注重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调和,以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研究强调治理的目标,体现了学派间的差异。同一学派中,同样存在不同。比如,美国罗威的“铁三角”与黑克罗的“议题网络”;英国理查森和乔丹沿袭美国研究传统,而罗茨、马什开始重视政治机构间的关系,从美国的微观视角转入中观视角;德国荷兰都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入手,但前者强调网络治理的新模式,后者强调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博弈管理强调在既有网络上的改变,而网络建构强调改变既有网络实现治理。异质性使得行动者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诉求,推动网络发展。
第三,角色性。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至今,至少扮演了三种新角色。一是新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已经成为英国及欧美政策制定过程研究的主要范式 [48],也是继多元主义—社会中心论、法团主义—国家中心论的新范式,有效促进了现代治理的研究与实践 [49]。二是新分析框架,政策网络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概念,与行为者模型结合,描述进而解释公共政策 [50],是西方政策分析领域的核心框架 [7],又如马什和史密斯(2000) [51] 提出的辩证分析模型(dialectical model),结合宏观环境、中观结构和微观行动者三个层面,指出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的辩证关系。三是新治理模式,这点尤其从治理学派观点而来,为公共治理提供新的途径。
然而,政策网络研究尚有争议。例如,决策机构是政策网络还是其他,网络特征是紧密还是松散、一致还是冲突,网络结构的作用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网络主体是个人还是团体,政策网络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这些问题存有分歧 [52]。因此,道丁(Dowding) [48]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策网络仅是一种隐喻,没有充分的理论解释能力,谈不上是一种理论。
Table 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network theory
表1. 政策网络理论的时空谱系
来源:作者自制。
3. 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中国实践
政策网络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今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进入21世纪,中国的研究趋势不断抬升,主要涉及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分析应用。
3.1. 理论引进
中国学者做了很多理论引进。朱亚鹏 [36] 梳理了国外政策网络理论的源流、发展和争论,介绍了概念、功能、特征以及研究视角,认为政策网络对政策过程具有理论解释力和分析力,对民主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描述性和价值规范性为我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蒋硕亮 [53] 从政策网络与政策过程、政策变迁的关系出发,总结英国学者集中在政策网络对政策制定影响的研究上,通过罗茨分类,发现强连接的政策网络有助于政策制定,弱连接则不利;荷兰学者补充了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的影响,认为虽然政策网络提供了比自上而下路径更好的方案,使得各主体互动、博弈,国家和政府不再是主导,但它们仍然有引导作用,指导政策执行,增强执行力;而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作用被认为是理论硬核,就是说行动者之间清晰或模糊的网络结构最终是用来解释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网络的结构、成员关系、信念以及外部环境也可能引起政策变迁。贾文龙 [54] 从政策网络在中国的兴起、运用、积极影响、负面效应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政策网络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等基础研究,和政策网络与政策过程、政策变迁和政策工具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意义,并对理论本土化提出希望。唐云锋和许少鹏 [55] 结合我国社会分层和差序格局、民主政治和传统文化以及城乡网络普及差距的背景,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认为政策网络应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要畅通利益集团进出渠道,平衡利益群体地位,将沟通交流、合作协商常态化、固定化和法律化。
有些学者聚焦政策网络的某一内容进行归纳。例如,蒋硕亮认为,政策网络理论作为政策分析的新范式,在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元、多层的网络化情况下,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视野,走出了阶段论的窠臼,实现了政策过程的图景转换 [56]。范世炜 [57] 从资源依赖、共同价值和共享话语三种研究视角分析比较政策网络,指出政策变迁分别与之形成三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映射模式,应根据具体情况,找出更适合、最具解释力的一种理论视角解释具体现实问题。陈建国 [46] 对政策网络研究进行理论审查,指出理论的缺陷、困境与争论,提出走向制度主义和回归网络本质是走出困境的两个方向;杨代福 [58] 由政策网络理论的缺陷,总结了萨巴蒂尔(Sabatier)和金肯斯–史密斯(Jenkins-Smith)倡导联盟框架、布隆–汉森(Blom-Hansen)新制度途径、马什和史密斯辩证途径、卡尔森作为集体行动的政策网络途径、新制度途径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以及政策网络途径与博弈论结合六种修正视角。
也有学者突出政策网络研究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情况,如结合经济制度,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借鉴集体行动理论,引入“社会学习”概念,加入理念的变量,整合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研究等等 [59]。或自己尝试引入新理论,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张体委 [60] 引入结构化理论,克服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构建统一的解释框架。
3.2. 中国之治中的理论应用
当政策网络理论引入国内到一定程度时,不少学者尝试结合国情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例如,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探究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61],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工具角色,指出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在于行动者的有限性和网络结构的封闭性 [62],利用罗茨模型,识别出十八大后反腐网络的不同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63],利用政策网络与政策执行、政策结果的关系,分析异地高考的政策网络、问题与出路 [64],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等核心观点,探析由邻避冲突事件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的政策过程 [65],利用议题网络,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存在的困境 [2]。
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政策网络实证研究颇有兴趣。例如,以山东省日照市150个城市气候变化倡议为例,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在地方气候行动中的作用、政策网络和合作关系的形成的分析,探讨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如何实现治理的转变 [66];以内地1998年至2010年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例,探索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同时指出中西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会导致政策制定研究方法上和实践上的困难 [67];以全球环境研究所和自然之友为例,探究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政府官员间创建政策网络改变环境政策 [68]。中国学者对国外案例同样关注,比如,以英国“邻里振兴计划”为例,说明政策网络的应用性和政府的导航作用 [8]。
4. 结论
政策网络理论在复杂的背景下形成,有多个理论源头,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兼具宏观微观中观研究视角,在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和治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色。政策网络理论存在缺陷与困境,但正是在争论中,得以有了概念演进和理论进化,成为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在该理论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政策网络的基本内涵、逻辑起点、学派观点、理论发展等内容作了详细梳理和介绍,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并尝试进行实证研究,海外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实证应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放眼未来,政策网络理论对中国之治有借鉴意义。第一,宏观视角下的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有利于分析中国之治的环境适应条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之治的具体表现,所有治理行为都是在制度体系下展开,关键在于制度优势能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的整体思维不容忽视。第二,多个研究视角有利于分析中国不同层面的治理。纵向看,中国之治呈现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治理层级;横向看,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69]。政策网络理论恰好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个人的治理分析提供宏观、微观和中观研究角度。第三,政策网络的治理模式为中国之治启发思路。在全球化和市场要素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行动主体彼此依赖,关系强化,政策过程具有跨国界、跨领域、跨层次、跨部门等特点,多元协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凸显出来,政策网络治理路径有利于破解零和博弈难题,实现正和博弈。
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其富于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治理借鉴,多元的理论观点启发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基金项目
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项目(22604217)。
文章引用
杨溢群,卢笛声. 政策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国之治中的应用
Policy Network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hinese Governance[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09(10): 1614-162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226
参考文献
- 1. Kenis, P. and Volker, S. (1991)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Analysis: Scrutinizing a New Analytical Toolbox. In: Marin, B. and Mayntz, R., Eds.,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25-59.
- 2. 周恩毅, 胡金荣. 网络公民参与: 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 100-103.
- 3. 李玫. 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 Börzel, T.A. (1998) Organizing Babylon—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 253-273. https://doi.org/10.1111/1467-9299.00100
- 5. 董幼鸿. 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政策评估制度建设——以政策网络理论为视角[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4): 83-91.
- 6. 丁晓强. “中国之治”的历史之维[N]. 中国教育报, 2019-12-05(05).
- 7. Hudson, J. and Lowe, S. (2009)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Process: Analysing Welfare Polic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olicy Press, Bristol. https://doi.org/10.2307/j.ctt1t895jd
- 8. 郭巍青, 涂锋. 重新建构政策过程: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9(3): 161-168.
- 9. 薛澜, 彭宗超, 张强. 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 管理世界, 2002(2): 43-56.
- 10. 陈振明. 中国公共管理学40年——创建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公共管理学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47-54.
- 11. Jordan, G. (1990) Sub-Governments, Policy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Refilling the Old Bottl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 319-338. https://doi.org/10.1177/0951692890002003004
- 12. 李瑞昌.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122-127.
- 13. Rhodes, R.A.W. (1997)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Political Science. In: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52.
- 14. 胡伟, 石凯. 理解公共政策: “政策网络”的途径[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4(4): 17-24.
- 15. 侯云.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J]. 河南社会科学, 2012, 20(2): 75-78.
- 16. 陈敬良, 匡霞. 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0(3): 97-105.
- 17. Griffith, E.S. (1939) The Impasse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the Modern Government in Action. Harrison-Hilton Books, Inc., New York.
- 18. Freeman, J.L. (1955) The Political Process: Executive Bureau-Legislative Committee Relations. Doubleday, Garden City.
- 19. Cater, D. (1965) Power in Washington: A Critical Look at Today’s Struggle to Govern in the USA. Collins, London.
- 20. Grant, M. (1966) Private Power & American Democracy. Random House, New York.
- 21. Lowi, T. (1969) The End of Liberalism. W. W. Norton, New York.
- 22. Ripley, R.B. and Franklin, G.A. (1976) Congress, the Bureaucracy, and Public Policy. Dorsey Press, Georgetown.
- 23. Heclo, H. and King, A. (1978) 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413, 46-57.
- 24. McFarland, A.S. (1987) Interest Groups and Theories of Power in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129-147.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00004683
- 25. Heclo, H. and Wildavsky, A. (1981) The Private Government of Public Money: Community and Policy inside British Politics. Springer, Berlin. https://doi.org/10.1007/978-1-349-16607-7
- 26. Friend, J., Power, J.M. and Yewlett, C.J. (2013) Public Planning: The Inter-Corporate Dimension (Vol. 5). Routledge.
- 27. Sabatier, P.A. (1988) 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of Policy Change and the Role of Policy-Oriented Learning Therein. Policy Sciences, 21, 129-168. https://doi.org/10.1007/BF00136406
- 28. Marsh, D. (1998) 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 Ope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29. Jordan, A.G. and Richardson, J.J. (1983) Policy Communities: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Policy Styl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1, 603-615. https://doi.org/10.1111/j.1541-0072.1983.tb00564.x
- 30. Rhodes, R.A.W. and Marsh, D. (1992)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Network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1, 181-205. https://doi.org/10.1111/j.1475-6765.1992.tb00294.x
- 31. Rhodes, R.A.W. (1990) Policy Networks: A British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 293-317. https://doi.org/10.1177/0951692890002003003
- 32. 朱亚鹏. 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6(3): 80-83.
- 33. Marin, B. and Mayntz, R. (1991)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 34. Powell, W.W.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AI Press, Greenwich, 295-336.
- 35. Mayntz, R. (1993) Modern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Knowledge and Policy, 6, 3-16. https://doi.org/10.1007/BF02692798
- 36. 朱亚鹏. 西方政策网络分析: 源流、发展与理论构建[J]. 公共管理研究, 2006: 204-222.
- 37. Scharpf, F.W. (1997) 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 Routledge, Abingdon-on-Thames.
- 38. Kickert, W.J.M. (1997)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An Alternative to Anglo-American “Managerial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75, 731-752. https://doi.org/10.1111/1467-9299.00084
- 39. Sørensen, E. and Torfing, J. (2016) 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 Springer, Berlin.
- 40. Kickert, W.J.M. and Koppenjan, J.F.M. (1997) Public Management and Network Management: An Overview. In: Kickert, W.J.M., Klijn, E.H. and Koppenjan, J., Eds., 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Sage Publications, New York, 35-61.
- 41. Klijn, E.H. and Koppenjan (2000)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Networks Foundations of a Network Approach to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heory, 2, 135-158. https://doi.org/10.1080/146166700411201
- 42. Klijn, E.H. (1996)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s: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8, 90-119. https://doi.org/10.1177/009539979602800104
- 43. Schneider, V. and Werle, R. (1991) Policy Networks in the German Telecommunications Domain. In: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97-136.
- 44. Vignola, R., McDaniels, T.L. and Scholz, R.W. (2013)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Using Policy-Network Analysis to Identify Key Organizations for Bridging Information across Scales and Policy Area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1, 71-84. 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13.03.004
- 45. Weishaar, H., Amos, A. and Collin, J. (2015) Capturing Complexity: Mixing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a European Tobacco Control Policy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8, 175-192. https://doi.org/10.1080/13645579.2014.897851
- 46. 陈建国. 对政策网络研究的理论审查[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2(1): 67-72.
- 47. Benson, J.K. (1982) 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 In: Rogers, D.L. and Whetten, D.A., Eds.,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mes, 137-170.
- 48. Dowding, K. (1995) Model or Metaphor?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Policy Network Approach. Political Studies, 43, 136-158.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48.1995.tb01705.x
- 49. Howlett, M. (2002) Do Networks Matter? Linking Policy Network Structure to Policy Outcomes: Evidence from Four Canadian Policy Sectors 1990-2000.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 235-267. https://doi.org/10.1017/S0008423902778232
- 50. Blom-hansen, J. (1997)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Policy Networks. Public Administration, 75, 669-693. https://doi.org/10.1111/1467-9299.00080
- 51. Marsh, D. and Smith, M. (2000) 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 Towards a Dialectical Approach. Political Studies, 48, 4-21. https://doi.org/10.1111/1467-9248.00247
- 52. Mikkelsen, M. (2006)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as a Strategic Tool for the Voluntary Sector. Political Studies, 27, 17-26. https://doi.org/10.1080/01442870500499868
- 53. 蒋硕亮. 政策网络: 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J]. 江汉论坛, 2011(4): 80-84.
- 54. 贾文龙. 近年来国内政策网络研究的述评与展望[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2): 150-158.
- 55. 唐云锋, 许少鹏. 政策网络理论及其对我国政策过程的启示[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2, 28(2): 40-45.
- 56. 蒋硕亮. 政策网络路径: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新范式[J]. 政治学研究, 2010(6): 100-107.
- 57. 范世炜. 试析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三种研究视角[J]. 政治学研究, 2013(4): 87-100.
- 58. 杨代福. 政策网络理论途径的缺失与修正[J]. 理论月刊, 2008(3): 82-85.
- 59. 刘海燕, 刘蕊. 国外政策网络研究: 概念逻辑、研究内容与研究展望[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0(5): 59-63.
- 60. 张体委. 超越结构与行动——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路径反思与“结构化”分析框架建构[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0, 22(3): 3-12.
- 61. 王春福. 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基于政策网络视角的分析[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7, 9(3): 8-9.
- 62. 朱亚鹏. 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与出路: 政策网络的视角[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61(3): 345-350.
- 63. 姚映雪. 十八大后反腐政策网络分析[J]. 党政论坛, 2018(5): 53-56.
- 64. 姚松. 异地高考政策运行特征、前景及出路: 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J]. 江苏高教, 2013(4): 43-46.
- 65. 李东泉, 李婧. 从“阿苏卫事件”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的政策过程分析: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1): 30-35.
- 66. Westman, L.K. (2017) Urban Climate Governance in China: Policy Networks, Partnerships, and Trends in Participation. http://ezproxy.library.dal.ca/login?url=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116930427?accountid=10406%0Ahttp://sfxhosted.exlibrisgroup.com/dal?url_ver=Z39.88-2004&rft_val_fmt=info:ofi/fmt:kev:mtx:dissertation&genre=dissertations+%26+theses&sid=ProQ:ProQu
- 67. Zheng, H., De Jong, M. and Koppenjan, J. (2010) Applying Policy Network Theory to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Urban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Public Administration, 88, 398-417.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99.2010.01822.x
- 68. Teets, J. (2017) The Power of Policy Network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ang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Governance, 31, 125-141. https://doi.org/10.1111/gove.12280
- 69. 郁建兴. 辨析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N]. 光明日报, 2019-08-30(11).
NOTES
1因翻译不统一,亦译为合作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社团主义、阶级合作主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