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ute Settlement
Vol.
06
No.
04
(
2020
), Article ID:
39527
,
7
pages
10.12677/DS.2020.64009
互联网背景下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路径研究
吴佳文
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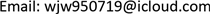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5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30日

摘要
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诉讼效率低下会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和保障,动摇人们对司法制度作为纠纷解决功能的信任。我国司法实践中诉讼效率低下现象比较突出。鉴于此,我国曾通过增加法官人数、提高法官素质以及完善民事诉讼程序的方式来提高民事诉讼效率,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却无法解决。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提升民事诉讼效率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立案、在线调解、举证与质证、庭审四个环节目前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的互联网路径。
关键词
民事诉讼效率,提升路径,互联网
The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Civil litig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Jiawen Wu
Network Space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Law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Nov. 25th, 2020; accepted: Dec. 23rd, 2020; published: Dec. 30th, 2020

ABSTRACT
Litigation efficiency is the basic value goal of civil litigation. Low litigation efficienc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exercise and protection of the parties’ rights and shake people’s trus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s a dispute resolution functio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 phenomenon of low litigation efficiency is quite prominent. In view of this,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judg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judges and improve the civil procedur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ivil litigation, although i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some problems exposed cannot be solv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ivil litigation. The us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ivil li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filing, online mediation, proof and cross-examination, court tria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easible Internet path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Keywords:The Efficiency of Civil Litigation, The Path of Improvement, Internet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诉讼过程中永恒的价值追求。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效率问题是人类最古老、最恒久不变的话题之一,从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对该问题有过锲而不舍的探究。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类民商事纠纷集中爆发。加之与未结案的纠纷累加,我国法院审判压力骤然增加。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要“快、好、省”地解决矛盾纠纷,而诉讼效率的核心也正是如此。
2. 民事诉讼效率的概念阐释
对民事诉讼效率进行阐释前,须对“效率”进行语义分析。在古汉语中并无“效率”一词,在英语中对应的单词是“efficiency”,有将其译为“效率”或“效益”。而在汉语中,“效率”和“效益”是意思并不相同的词语。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效率”与“效益”作适当区分,他们认为在论及司法活动中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时,效率所要描述的应当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尽可能又多又快解决纠纷,充分利用和节省各种诉讼资源 [1]。而效益强调的则是结果的好 [2]。效率虽然强调要充分利用和节省各种诉讼资源,这并不代表诉讼效率等于经济效率,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诉讼效率中的效率虽源自于经济领域,但诉讼中的效率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经济学的效率本质上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诉讼产出是以诉讼是否公正来衡量,而经济产出通常以产品和金钱来计算。并且经济效率强调的是结果,而诉讼效率更强调过程,没有诉讼过程就没有诉讼效率。故本文所述的民事诉讼效率是指民事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
3. 如何看待我国民事诉讼效率
人们认为,法院工作缓慢一直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疾病。莎士比亚可能厌倦了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效率低下,通过哈姆雷特的话,指责“法律的拖延”,并认为这是人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弊病”之一。如何提升民事诉讼效率是所有法律制度共同的问题。毫无疑问,我国的人民法院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尽管多次开展旨在加强法院管理和案件管理的运动,但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效率低下。2013至2017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审结、执结8598.4万件,这表明仍有3.3%的案件经过4年的时间仍无法审结或执结。2018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5.1万件,审结、执结1379.7万件,11.85%的案件未得以解决;2019年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3156.7万件,审结、执结2902.2万件,未审结、执结案件仍有8.07% [3]。受理案件数量与未审结、执结案件数量的双增加,表明了我国存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严重问题。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及时结案,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是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有一些人认为民事诉讼效率不高有时是一件好事,比如对被告而言,其总是希望将裁判的时间向后推迟,而且从制度上说,诉讼案件迟迟没有结案,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当事人和解。但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之一即是效率,追求诉讼效率的提高也成为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方向。这是因为如果不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会带来更大的可能性错误,以及对司法的损害。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有损于司法公信力。如不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部分案件一直没有结案,案件的矛盾纠纷就无法得以解决,案件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容易产生过激情绪和行为,造成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出现民众对司法不信任,最终影响社会稳定。第二,影响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增强案件判决结果失误的可能性。诉讼案件拖延的时间越长,判决准确性就越低,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取证难度的增加以及某些重要证据的灭失,必将导致事实难以查明甚至无法查明,比如证人记忆模糊,证人可能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导致法院很难或不可能得出一个公正结论的消极后果。同时,证据的难以取得和无法取得还会引起本身无理由一方当事人的态度变得强硬,从而影响以速调的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第三,损害诉讼判决结果的可执行性。执行难已成影响我国司法权威的一大难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除了有关执行立法上的缺陷,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诚信度低等社会上的不利因素外,诉讼效率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裁判等待时间过长,事过境迁,实际执行时会出现无法执行或执行也没有实际意义的情况。
4. 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的历史实践
(一) 增加法官人数
曾经实务界多数人主张通过增加法官人数来提高民事诉讼效率。与西方发达国家法官人数相比,应该说,我国的法官人数总体上是比较多的。目前,中国各级法院共有21万多名法官,按13亿人口计算,每万人中约有1.6名法官。英国的正式法官为964人,0.58亿人口,每万人中不到0.17名法官。而日本全国共有2215名法官,1.23亿人口,每万人中只有0.18名法官。按法官在人口中的比例来比较,我国法官的数量是英国9.4倍,日本的8.9倍 [4]。我国法官人数在量上的优势并没有在审判效率上显示出任何优势 [5]。况且,增加法官人员涉及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编制的增加等诸多问题,故增加法官人数只是提升民事诉讼效率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长效的手段。
(二) 提高法官素质
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人世”,作为法律化身的法官,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素质,其中业务素质对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最为关键:业务素质高的法官,专业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办案效率高,周期短,且办案质量有保证,错案率低。提高法官素质是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的方法之一。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官法》作了重要修改,对法官的业务素质作了更严格的要求:法官的最低专业要求是“具备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并且“初任法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取得法学硕博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可以分别放宽至四年、三年”。虽然这些规定对今后的法官选任提出了更加专业、严格的要求,但对提高已任法官的业务素质水平却无帮助。长期以来,我国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倡导司法诉讼走“人民化”路线,部分已任法官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且因年龄等问题导致进修学习能力较弱,不能胜任当前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审判工作,因而使得民事诉讼效率不高。通过提高法官素质的方式来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本身就是一种漫长且低效的方式。
(三) 完善民事诉讼程序
如果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缺漏,那么民事诉讼效率必然会受其影响,无法提高。在201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关于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新变化,如小额诉讼制度、应诉管辖制度、直接送达制度和电子送达制度等。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均能提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效率,但在诉讼实践中,一些制度适用中的不当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在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情况要依法转换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条明确规定,对不符合小额诉讼案件条件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因为我国审理案件的程序转换的审批权限均为承办法官,对程序转换的审判流程没有完备的监督管理体系,极其容易造成承办法官随意转换规避审限超期,如果在简易程序审限内无法审结的案件,都以“不宜适用”这一个模糊标准来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时间定会增加,民事诉讼效率因此大大降低。因此,完善民事诉讼程序是需要不断的实践探索,发现新程序、新制度的不足之处,才能真正的提高我国民事诉讼效率。
5. 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的互联网路径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力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实行网络强国战略,将互联网发展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撑。2013年以来,我国法院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探索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领域、新模式,网络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框架初步搭建。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民事诉讼效率是当今时代的重要选择,笔者对立案、在线调解、举证与质证、庭审四个环节,依据目前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的互联网路径。
(一) 完善网上立案系统
我国法院现已依托互联网技术,大力推进网上立案,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诉讼服务渠道,规范诉讼服务流程,提升诉讼服务效率与质量。当事人通过电脑或手机端即可享受全天候在线自助服务,完成在线咨询立案、提交诉讼材料、交纳诉讼费用等操作。事实上,期望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来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效率,不是开通了网上立案诉讼服务平台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仍需完善优化网上立案制度与软硬件设计。
网上立案的推广适用必须与当事人程序自由选择、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进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网上立案应当对不同的使用主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的诉讼案件,除特殊情形外,引导案件代理律师适用网上立案。但对于一般的案件当事人,因网上立案操作较为复杂,且需具备立案的基本知识技能,因此,在网上起诉,可能会因安全性、技术性问题、操作失误或法律理解偏差导致诉讼拖延,影响诉讼效率。
对此,为平等保护线上起诉当事人的诉权,提高诉讼效率,在互联网信息化诉讼服务平台或立案软件设计中,应当配套立案步骤融入相应的操作指南与注意事项等流程信息,可采取文字、图示或视频演示等多种形式。例如,《吉林电子法院网上诉讼指南网上立案篇》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指导;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电子诉讼文书(含线上起诉)服务平台”提供线上起诉操作的录屏影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立案系统可为使用者提供问答环节,提供法律诊断,起草合适的文件 [6]。对非网民群体而言,因技术壁垒和应用成本可能在客观上形成新的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诉讼权利平等的分化,降低了诉讼效率。为了更好践行司法为民,让公众获得更为便捷高效、惠而不费的司法服务 [7]。对此类人群,应当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其诉讼能力的不均等。从诉权保障优于技术应用考虑,网上立案不能成为非网民的义务,否则会强化现时社会分化或产生新分化,导致该群体被边缘化的风险。从提供差别化诉讼服务着眼,法院可借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服务”机制,对存在阅读困难、视听障碍或身体机能受损等特殊主体提供必要帮助。可以在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妇联等组织设立网上立案服务台,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非网民群体当事人前往特定场所,由专门人员辅助当事人完成立案 [8]。当前部分法院已尝试对网上立案进行专门指导或提供法律援助。例如,《江苏法院网上立案登记工作流程规定(试行)》第11条规定,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自助立案功能区……落实专人指导当事人申请网上立案。
(二) 优化在线调解平台
在线调解与线下调解相比,在空间与时间上都具有明显优势,这正是在线调解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因。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法院在线调解机制对于当事人而言,多了一种程序选择权;对于法院而言,也发挥了便民利民的功能 [9]。另一方面,在线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缓和社会矛盾、分流诉讼案件的重要一环,具有源头解纷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在线调解需要公正且高效的解决纠纷,让每一个纠纷主体真正化解纠纷矛盾,避免其继续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故在线调解机制化解纠纷的效率高低与否,将直接影响民事诉讼效率。
目前我国各省一部分法院借助“移动微法院”微信小程序或者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开发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在线调解工作;一部分法院则依托自主开发建设的平台进行在线调解。当前我国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多已具备智能问答、在线交换证据、在线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等基础功能,同时“移动微法院”微信小程序在省(市)区域内的全面普及为纠纷主体提供了便捷高效解决纠纷的桥梁;其次,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多已贯通调解、在线立案、送达等流程,有效降低了当事人的程序担忧;最后,在资源共享方面,部分省市已建成实现区域资源整合、多元调解力量相衔接的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如“重庆法院纠纷易解”与“浙江ODR”在线调解平台吸纳区域内专业的优秀调解员注册上网,衔接仲裁机构与各调解组织,为纠纷主体提供多元解纷资源。在线调解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短板与不足。发展差异较大,重复建设现象突出。发展差异较大主要指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地区发展不平衡则具体表现在平台覆盖度、平台功能这两方面。从在线调解平台覆盖度方面考察,有些平台在全省范围内运行,而有些平台仅在市、县范围内运行。在平台功能建设方面,一般性的智能问答、线上生成调解协议及在线确认调解协议司法效力等方面的建设虽取得显著成效,但调解过程中辅助工具的应用仍存在着发展差异较大、不够普及的问题。其次,在线调解平台建设亦存在重复现象。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发达的省市,其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建设齐头并进,区域内拥有多个可供使用的在线调解平台,在浪费建设成本的同时,信息与资源的隔阂也加重了调解工作者与当事人的困扰。
为了提高在线调解机制化解纠纷的效率,应注重整合优化在线调解平台。第一,各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应先行整合辖区内法院现有的在线调解平台,融合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在线调解平台。对于在线调解平台建设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可先行引导辖区内法院对接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在线调解工作。第二,对于已有核心功能的平台,其具体业务功能和服务可以争取采用接口的方式对接现有的成熟产品 [10]。这样一方面既可以减少建设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平台功能快速上线,投入使用。第三,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专业性行业性调解资源,完善衔接配套的多元解纷体系。完善与其他解纷平台的联系,实现解纷资源共享,即在完善自身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与其它调解平台相对接,主动汇集多方调解资源,促使覆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领域的优秀调解员注册上线,延伸在线调解机制的神经末梢。通过由法院牵头整合优化社会调解资源,既有利于提高调解资源的利用率,也能够提高在线调解机制化解纠纷的效率和民事诉讼效率。
(三) 创新在线诉讼举证与质证方式
在线诉讼作为一种新型审判方式,其给传统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诉讼行为方式带来影响的同时,使得传统证据展现出了新的形式和特征。传统证据需要借助于电子设备才可以完成向在线诉讼中证据的转化。而在线诉讼中的证据的生成、存储和传递等环节均需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来完成,任何差错都有可能导致在线诉讼中的证据发生难以察觉的改变,会使得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非议。加之在线诉讼中的证据都以电子形式存在,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和保障司法公正的核心,不仅给当事人之间的充分质证带来了难题,也给法官的准确认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保障,创新在线诉讼举证与质证方式,不仅是努力实现法律真实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也利于提高民事诉讼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已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较多的在线诉讼规则,却对证据保管方面未作出详尽的规定。但是,证据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会面临毁损和灭失的风险,证据资格以及证据价值也都很有可能遭受破坏,相关案件事实无法得以认定,案件也会久拖不决,从而影响诉讼效率。在线诉讼中的证据都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诉讼双方通过互联网在线诉讼平台提交证据后,可能面临篡改、损毁的风险,因此保障互联网在线诉讼平台的安全性,防止诉讼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发生篡改或灭失的情况,杜绝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困难情况的发生,以此保障及提高诉讼效率。针对在线诉讼中电子证据保管难得问题,积极探索“区块链 + 司法”模式,以大数据、云存储和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利用区块链技术防伪造、防篡改的优势,能够大幅提高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设“天平链”电子证据平台,被纳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首批备案的区块链单位,完成跨链接入区块链节点18个,实现互联网金融、著作权等9类25个应用节点数据对接,在线采集证据数超过472万条,跨链存证数据达1000万条。
(四) 提升庭审智能化水平
在2020年初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的特殊时期,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当事人聚集、人员流动以及降低传播风险,法院作为公共场所,不可避免地需要从疫情防控角度出发而暂停线下庭审的情况下,但审判活动不能因此暂停。为保障庭审活动的如期开展,各级法院积极行动,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的电子诉讼平台建设,将司法审判方式从物理空间移步至网络空间,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深度凸显了民事电子诉讼庭审程序的高效与便捷。我国各地法院开展线上庭审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依托互联网专业通讯平台,搭建远程音视频实时沟通系统;二是利用移动微法院平台实现在线庭审;三是研发专门的“互联网开庭”程序;四是利用微信、“钉钉”等具有视频会议功能的网络系统开展庭审活动 [11]。总体来看,上述功能仍相对单一,主要满足于庭审各方在线交流,但无法利用进一步系统拓展审判智能化水平。
智能化低、功能的单一会导致线上庭审这一司法审判方式无法常态化使用,无法真正实现高效与便捷的初衷,民事诉讼效率提升不显著。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规定:“加大在办案平台建设、在线诉讼流程、新兴技术应用、在线诉讼规则等方面的探索力度;加速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智能化水平,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应用。”对照这一目标要求,需要在几个方面实现技术突破。一是运用推广人脸识别技术。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在精度、稳定性和速度方面已日趋成熟,能够满足普遍的实用化需要。使用人脸识别进行身份核对,关键是要取得人脸数据库资源的使用授权。当然,使用人脸识别比对成功后,仍要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和披露,以满足庭审各方的需要。二是实现语音同步转写。实践中普遍存在语音转写延迟问题,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语音转写系统服务器的功能,提高语音转文字的处理速度、性能,同时还应优化线上系统传输功能,实现既“转得快”,又“跑得快”。当然,庭审笔录只是庭审活动的记载,忠实、客观记录各方在庭审中表达的内容是其首要功能,笔录内容展示延时,在客观上不会也不应影响到庭审程序的正常进行。三是深度利用电子卷宗。庭审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对于法官而言,个案的审理包括了立案、送达、接收材料、证据交换、开庭、议决、文书撰写等诸多程序,解决了利用互联网开庭的问题,意味着其他程序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卷宗的深度利用因此显得尤其必要。应当借助线上诉讼活动的推行这一契机,全面升级人民法院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将已有的电子卷宗资源系统运用到线上庭审的各个环节,能够使线上庭审活动更加名副其实。
6. 结语
民事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提高诉讼效率是任重而道远的。而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也是永不停息的,仍应继续分领域、分步骤、分层次统筹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民事诉讼效率,对每一诉讼环节进行变革与优化,使其高效、便捷与公正,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司法便民。
文章引用
吴佳文. 互联网背景下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路径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Civil litig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J]. 争议解决, 2020, 06(04): 54-60. https://doi.org/10.12677/DS.2020.64009
参考文献
- 1. 凌永兴. 民事司法改革中的诉讼效率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10-11.
- 2. 谭世贵, 黄永锋. 诉讼效率研究[J]. 新东方, 2002(1): 33-34.
- 3.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R].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2): 366.
- 4. 陈文兴. 法官员额制度比较分析[J]. 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0(4): 352-355.
- 5. 詹建红. 法官编制的确定与司法辅助人员的设置——以基层法院的改革为中心[J].法商研究, 2006(1): 63-69.
- 6. 英国在线纠纷解决顾问小组<江和平译>. 英国在线法院发展报告(节选) [N]. 人民法院报, 2017-5-5(8).
- 7.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乌镇共识[EB/OL]. 2016.11.17.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11/id/2352002.shtml, 2020-8-11.
- 8. 王琦. 法院网上立案的实践检视及路径研究[J]. 法学杂志, 2016(11): 98-105.
- 9. 董青梅, 陈建丽. 在线调解“再塑新时代”枫桥经验[J]. 人民法治, 2018(1): 127-130.
- 10. 史甜甜. 我国法院在线调解机制的运行现状与完善[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20(9): 51-59.
- 11. 高鸿. 互联网庭审的功能和规则构建[N]. 人民法院报, 202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