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09
No.
07
(
2019
), Article ID:
31205
,
9
pages
10.12677/AP.2019.97148
Neuro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Yuan Yuan
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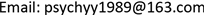
Received: Jun. 14th, 2019; accepted: Jun. 28th, 2019; published: Jul. 9th, 2019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ross-disciplinary field, neuroeducation, adhering to “brain-based, brain-adapted, brain-promoted” guideline, unfolds a large scal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Neuroeducation adopted arguments and ideas from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on pedagog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who took their roles in the form of “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 Neuroeducation employed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neuroscientific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opics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t mainly focused on neural “critical period”, neural plasticity and neural reuse, and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brought out lots of valuable achievements implicated f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especially primary edu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d their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interest training, potential excavation, as well as observational learning.
Keywords:Neuroeducation, Observational Learning, Neural Plasticity, Potential Excavation, Mirror Neuron System
神经教育学与儿童教育
袁媛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康复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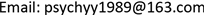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9年6月14日;录用日期:2019年6月28日;发布日期:2019年7月9日

摘 要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神经教育学立足于“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的方针和原则来开展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神经教育学汇聚着来自教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学科内积极形成“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巧妙的研究设计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教育和教学实践及其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探究,围绕神经元发育“关键期”、神经复用和可塑性以及镜像神经系统等主题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并给人们,尤其是儿童教育及教学实践带来了诸多启迪。研究就神经教育学成果对小学儿童教育密切有关的兴趣培养、潜能开发、以及观察学习的潜在启示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神经教育学,观察学习,神经可塑性,潜能开发,镜像神经元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儿童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关注的重点内容,而且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主题。儿童身心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及其教育的重要性,使其受到人们和媒体的格外重视。暂且不谈“择校”现象所透视的教育公平问题(吴永军,2012),“择校”现象如此普遍和严重,它也是人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以及对优质教育诉求的客观反映。各类商家或许正是看到了这其中所潜藏的巨大商机,导致诸如“赢在起跑线”或“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宣传单页充斥着大街小巷,家长带领或强制小学儿童参加各类兴趣班和特长班的媒体报道亦层出不穷。此类宣传标语或现象也日渐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或交际生活中难以避谈的话题。然而,这一切却苦了孩子,不仅使他们需要承受自己所无法承受之“重”,而且导致他们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效果大大减弱(李萍,2012)。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儿童教育,尤其是小学儿童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切实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有着十分重要教育和现实意义。
神经教育学1(neuroeducation),亦称教育神经科学(educational neuroscience),是将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发展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深度整合,提出科学的教育理论、践行科学的教育实践的、具有独特话语体系的一门新兴学科(李其维,周永迪,2011;周加仙,2009)。该学科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它不仅是一门超越学科界限的新学科,而且是一门深度整合和跨越了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学及其实践等诸多学科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e);它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在充分汲取传统教育学人性观的基础上力倡从大脑和神经生理层面来解构和建构客体知识、教育实践和学习者的关系,主张从大脑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和神经元复用(neural reuse)来解读人类知识学习、技能获得和智慧产生的过程与机制;另一方面重视和强调神经教育学研究的应用和实践意义,主张神经教育学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教科书中“陈述性知识”层面,应当能够为人们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进、以及教学改革与设计等各类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从某个意义上而言,应用性或者实践性是神经教育学的首要特征,它是超越了传统的任何一门“大”教育学2的。以往没有哪一门“大”教育学像神经教育学这样,不仅强调教育学的研究和理论意义,而且更重视研究成果的实践和应用价值。神经教育学立足于严谨的科学设计,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和成果来深化人们对学习的理解,不仅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周加仙,2010),而且强调在与教育实践充分结合和互动基础上,力图通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来消解教育实践中的各类“神经神话”(neuromythologies),形成并创造教育和教学相关的合理的科学知识。神经教育学原理不仅在教育学家中,而且在教师中,都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拥护。同时,神经教育学还可以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决策者提供参考和建议,以科学实据来开展教育规划与教育实践和改革(陈巍,张静,陈喜丹,丁峻,2010)。许多神经教育学家确信,教学不考虑神经心理学原理则是盲目的教学,将会导致弱化学生脑活动的自然机制,而要恢复这些机制,将会比自然教学过程复杂得多慢得多。综上可知,无论神经教育学功能定位的初衷中是否是专门为教育决策者和参与者提供参考或指导,但它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或启迪均是伴随并被其快速发展过程所检验过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本研究将侧重就神经教育学对儿童教育的启示进行探讨和阐述。
2. 神经关键期与兴趣培养
关键期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关键期”概念最初原自于动物研究。早期对动物视觉发展的研究发现,若在动物出生后不久就蒙上其一只眼睛,这种早期的视觉剥夺会严重影响动物视觉皮层的神经联结,以致使得遭受视觉剥夺的眼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发挥其正常的视觉功能。然而,这种视觉剥夺对成年动物的视觉似乎并没有影响。类似的,人们在人类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键期。经典发现便是熟知的具有先天性白内障的儿童3~5岁时去除白内障无法恢复视觉,但成年白内障者通过该手术则可恢复视觉,意味着生命早期阶段有个视觉发展关键期(秦金亮,2008)。人们随后发现,语言学习和运动技能(比如器乐学习、运动技能的获得等)发展亦可能存在“关键期”(王亚鹏,董奇,2010)。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有学者发展出了“关键期”概念,并主张大脑及其功能的发展存在“关键期”或“敏感期”,若错过了该时期,那么相应认知功能的发展将会产生难以弥补的后果。
关键期概念的提出催生了一些“神经神话”。所谓神经神话就是指在解释和应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时所出现的简化、夸大或歪曲科学事实的现象。例如,人们经常听到的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0~10或者0~3岁的关键期(Bruer, 2002)。在该时期内,儿童的语言、动作和运算思维等都快速发展,若错过了该时期,神经突触增生结束,所谓的“机会之窗”关闭,许多认知和心理机能都将永远消失。错过了这个机会,某些学习不会有效果。类似的,“丰富环境能够学习”的神经神话认为,丰富环境刺激加快了突触生长,促进了脑发育。突触越多,突触被修剪或消除的越少,神经活动的潜力就越大,儿童的学习就越好,脑力就越强,将来的成就越大。当然这些确实存在一定的科学依据,毕竟心理机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例如,早期皮亚杰有关儿童研究所揭示的儿童思维和道德发展阶段都是儿童心理发展可能具有关键期的经典证据。但应当认识到关键期的相对性和神经发展的可塑性,不应对关键期作静待观。因为许多时候,某些人依据关键期的相关发展做出了不适当或过度的推论,导致形成了神经教育深化。也许正是受该神经神话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学前和小学阶段儿童课外教育与兴趣培养有着异常兴趣,并催生了大量所谓的兴趣培养机构。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强迫孩子参与兴趣培养班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儿童教育。它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儿童父母的儿童观,例如,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父母的“梦想”与“期望”的载体等;另一方面与“神经神话”密切相关。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其中,儿童的天性观其最基本的内容。儿童最大和显著的天性是游戏或玩性,即好奇与不受拘束的自由探究。父母强制儿童或小学生参与各类兴趣培养班不仅侵占了小学生自由和不受拘束的自主探究的时间,而且容易导致儿童“过度”的学业负荷。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们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使“天真活泼的孩童”变成“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罗祖兵,杨娥,2013);而且抑制了学生的个性。过多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兴趣的培养促使儿童的生活单一,整天“泡”在单调的书堆、琴谱和歌词中,导致孩子的情感、个性和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或严重缺失。儿童阶段是健全人格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的阶段,童年期经验或记忆会影响个体一生的发展。个体的童年经历和情绪记忆将会被大量存储在大脑的杏仁核之中,这些童年经验对个体人格与个性发展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换言之,家长在某些“关键期”所设置的“丰富刺激”,以及由此所致的让孩子参加兴趣班的做法收效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有悖初衷。
新近的神经教育学研究显示,“关键期假设”仅仅是对某些脑研究或科学事实的推测,人类仅仅对视觉发展的关键期有所了解,对其他感觉和运动系统的关键期知之甚少(袁学松,2012)。对关键期机制的了解微乎其微,无法预测某个儿童在哪个年龄点出现“关键期”。虽然关键期与突触增生有关,但已有研究仅仅支持感觉、运动系统以及语言的某些方面存在关键期,尚不知道文化知识传授系统是否有关键期,儿童社会交往、正规学校教育如阅读、数学等方面是否存在关键期,也还不了解突触增生在这方面技巧的获得中起怎样的作用。学习特定技巧的关键期是基于进化和种系发展的结果,受遗传基因控制。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社会和文化活动,与关键期相关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教育实践(Bruer, 2002; 乔文达,董奇,2006)。不仅如此,并不是像“关键期”假说所假设的那样,“关键期”的错失可能也不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关键期”相应的认知功能就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只不过在所谓的“关键期”大脑对某些刺激比较敏感,即是说大脑发展存在敏感期(袁学松,2012;王亚鹏,董奇,2010)。错过“敏感期”并不意味着机会的完全丧失,但可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弥补因错过“敏感期”而造成的认知发展滞后。在此期间,若为儿童提供适应的环境和学习条件仍能促使其认知功能得到适宜的发展。但是,过度、过量或者过早地进行不合理和不科学的早期教育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正如韦钰院士在《运用当前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报告中指出的,“脑从出生前到20岁左右是建构期,这个过程是连续渐变的,所有的教育,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都有生物基础相伴,而且受其限制。学生并不是一张白纸,教育应该根据他们已有的生物基础来开展。5岁之前背唐诗,不仅无法对幼儿起到积极影响,反而会影响到儿童未来创造力的发展”。何况,大脑“关闭”了某个认知机能之“门”后,还会在适当时候“打开”另一扇“窗”。换言之,大脑具有认知机能的补偿性。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有关盲人和聋哑儿童的研究。许多研究显示,盲人或聋哑儿童可能会存在严重的视力或听力障碍,但他们的意图理解能力、想像能力和触觉都较正常人要发达(Goldreich & Kanics, 2003)。总之,神经教育学研究启示人们应当科学认识神经发育关键期对小学生教育和兴趣培养的作用,谨慎应用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并科学地甑别“神经神话”,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小学生兴趣培养和由此所增加的“负担”之间的关系,避免小学生因为额外的兴趣培养错失了正处于关键期的认知机能的快速发展机会,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学习兴趣枯竭、学业不良甚至发展或者人格障碍等。
生物体神经发育关键期的发现虽然对于生物学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与小学儿童教育的直接启示严重脱节(陈巍等,2010)。神经教育学成果一方面启示人们:儿童或小学生的教育尤为重要和关键,不仅对儿童认知能力的促进和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儿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也有着十分甚至更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提示小学儿童家长或教育工作者应当正确认识和甑别“神经神话”,并科学认识到教育并非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过量、过早甚至过多迫使儿童参与各类兴趣培养项目,不仅增加了孩子的“负担”,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抑制了其正常的情感、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罗祖兵,杨娥,2013),而且导致他们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竭,产生不良的童年经验,以致影响孩子的毕生发展。
3. 神经元复用与潜能开发
虽然神经发育过程存在关键期,并且关键期内特定技能的训练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传统教育学和心理学对于关键期教育的实施又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关键期概念具有双刃剑的威胁:一方面有助于通过针对性训练来促使儿童心理能力正常和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可逆”的消极影响会打击某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信心(陈巍等,2010)。为了澄清有关关键期的理解误区,神经教育学对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复用(neural reuse)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脑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巨系统,其结构和功能虽是在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受学习、训练以及经验等影响,使得大脑皮层产生结构改变和功能重组,即神经可塑性。先前研究普遍揭示,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只有处于发育的早期阶段均具有较强的神经可塑性(王亚鹏,董奇,2010),即各项认知机能基本通过科学得当的训练均能有所增进。最新研究显示,中枢神经系统不仅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可塑性,而且在其发育成熟以后仍然存在可塑性。虽然在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以后其可塑性可能没有所谓的敏感期强,但在大脑发育成熟以后,这种因经验引起的大脑结构与功能的改变可能比最初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经过锻炼或技能学习、成人的大脑,即使是老年人,依然可以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在经过6个月的有氧锻炼后,老年组的前额叶、颞叶及顶叶的灰质和白质容量增加,而青年组却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老年组的这种锻炼获益减少了脑容量萎缩的风险(杜新,陈天勇,2010),在前扣带皮层、右颞上回、右侧额中回与白质连接度降低了42.1%,33.7%,27.2%与27.3%。经过三个月甚至一周的接抛球杂耍训练后,杂耍学习者负责运动信息存储与加工处理的脑区(如颞中区、顶内沟)的灰质容量均出现了显著的延展,即使老年人也能出现相同的增长(Boyke, Driemeyer, Gaser, Buchel, & May, 2008),且大脑白质亦可因训练而增长(Scholz, Klein, Behrens, & Johansen-Berg, 2009)。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神经元不仅具有可塑性,而且还具备复用(reuse)功能。神经元复用有别于常规理解的神经可塑性,神经可塑性或者只能视为神经元复用的一种类型。依据神经元复用观,神经环路在形成初始或原初的功能后,仍可继续习得新功能,并且新功能的习得无需个体暴露或沉浸于可能致使该环路或其他环路初始功能丧失或受损的环境,同时也无需该神经环路结构或局部结构的改变(Anderson, 2010)。目前有关语言、空间认知、算术认知以及诸如工作记忆和概念隐喻等高级认知领域的诸多研究均支持神经元复用观点。
不时就可以在形形色色的杂志或报刊上看到人脑潜能开发的广告。日常生活中,潜能开发非常普遍。各类商家和媒体有关潜能开发的“科学”证据主要是诸如“人脑开发不足10%”等各类“神经神话”。在传统基于脑的教育研究中会找到许多不合时宜甚至不严谨和科学的论断。其实,脑潜能开发的科学依据应是神经元复用和神经可塑性。就小学儿童教育而言,许多家长嘱托和带领甚至强迫孩子参加各类特长班和潜能开发班,极力想通过这些所谓科学的潜能开发活动大大地提高孩子的大脑开发和利用程度,以使孩子能够出类拔萃,成为现在或未来某个领域的佼佼者。来自神经教育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尽管技能训练能够促进小脑或者大脑的发展和成长,但它们均存在前提。这意味着,潜能开发并不是无条件和无节制的。且不论人脑有多少潜力可以开发,无论当前人们观念中熟知的“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脑能力的10%”还是“爱因斯坦也只用了30%”均表明人脑还存在绝大多数的大脑潜能未被开发。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假定人脑潜能是无限的,但脑潜能开发者在鼓吹开发无穷无尽的潜能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大脑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大脑是能量依赖的,依赖于血液运送的能量。换言之,大脑作为学习与思维的“硬件”,受到营养的影响。不仅如此,大脑还是高耗能器官。既有研究显示,脑血流量占心输出量的15%,且仅占体重2%的人脑的耗氧量则占全身总耗氧量的20% (唐嘉忠,王伟,2011)。大脑是血糖依赖的,任何脑能或潜能的开发与训练都会产生血糖消耗并需要心脏的血糖供应。只有保持正常血糖水平,才能有效保证大脑的葡萄糖供给。根据儿童或小学生的心身活动特点,他们非常容易产生脑部供血不足。因为他们不仅会面临大量来自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甚至兴趣培养或特长班的血糖消耗,而且受儿童或小学生意志控制力弱以及好奇心强等的影响,他们会参与各类游戏或同伴活动并产生大量的体能消耗。
由上可知,潜能或脑能开发虽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且对个体的发展有相当好处。然而,各认知功能在整个生命全程均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但不同时期所表现出可塑性的强弱、敏感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性很不相同。儿童监护人及其教育工作者需要科学认识与理解潜能开发,根据科学规律,在保证不增加小学生的教育“负担”、正确甑别“神经神话”与科学认识潜能训练效果的前提下,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适度的潜能开发和训练。
4. 镜像神经元与观察学习
神经教育学中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是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及其教育应用的探讨(van Gog, Paas, Marcus, Ayres, & Sweller, 2009; Elliott, Grierson, Hayes, & Lyons, 2011; 陈建翔,陈建淼,2011;陈巍,汪寅,2013)。镜像神经元最早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一类独特的神经簇团。Rizzolatti的实验小组在研究猴脑前运动区的单个神经元放电时,发现其F5区的神经元既能在猴观察其他个体做动作时放电,也能在猴自己做出相似动作时放电。他们将两种条件下放电模式相似的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并推断该神经系统可以使得个体把观察到的动作“直接映射”到自己的运动体系中,从而获得来自“内部”的理解,并快速判断他者的动作目标和意图(陈巍,汪寅,2013;Rizzolatti, Fadiga, Gallese, & Fogassi, 1996)。近年越来越多的无损脑成像研究重复观察到人类也存在镜像神经系统。该系统的发现不仅对人们认识动作识别、意图理解、行为模仿、共情以及心智阅读的心理机制有重要价值(胡晓琴,傅根跃,施臻彦,2009),而且对推动教学改革与教育创新也有着显著意义。
“做中学”是一个深刻影响着教育实践和变革的理念。该理念的倡导者——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和重新组织”、“教育即生活”,教学就是通过儿童主动活动去检验一切和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他特别强调学生的本能和兴趣,认为“从做中学”时必须排除由于外部强制或命令的行动(单中惠,2002)。杜威主张不应当将学习知识从生活中抽取和孤立出来作为直接追求的事件,教学不是直截了当或“填鸭式”注入知识经验,而是诱导儿童或学生在生活和活动中得到经验和知识。因此,他建议取消讲授,主要采用答疑和活动作业,倡导在互动和活动中促进学生的“生长”。“做中学”具有诸多优点:它促使在“做中学”活动过程中,学生需要在讨论时倾听他人的发言,在分工合作时共享实验材料,在别人需要支持时及时给予帮助,在小组讨论意见发生冲突时及时解决等等。这些意味着学生不仅需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还要求他们能够及时察觉他人的情绪变化和想法,以做出及时的反应(杨元魁,叶兆宁,2011)。这些将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同理心、共情、意图理解能力以及心理理论的“生长”和发展。或许正是由于“做中学”促进人的健康“生长”之显著功效,导致它占据着推动和影响教育深刻变革理念的中心位置长达近百年之久。
研究显示,观察学习(learning-by-observation)和做中学(learning-by-doing)所引起的神经功效无显著差异(van Schie, Mars, Coles, & Bekkering, 2004; Yu & Zhou, 2006; 袁媛,刘昌,沈汪兵,2012)。此中最典型的即观察学习与镜像神经元关联性的发现。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和动物的观察学习均与各自的“做中学”有着相似的神经激活——“做中学”过程激活的运动皮层区均在观察“做中学”相同或类似操作活动的观察过程呈现出同等激活模式(Petrosini, Graziano, Mandolesi, Neri, Molinari, & Leggio, 2003; Buccino & Riggio, 2006),甚至有研究发现,个体“做中学”过程中所激活脑区的时程和强度指标——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及其波幅与观察学习过程中的指标非常一致(袁媛等,2012)。如前所述,表征观察学习关键神经机制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亦是参与意图理解、同理心或共情、行为模仿以及心理理论的重要机制(胡晓琴,傅根跃,施臻彦,2009),即支持观察学习与“做中学”具有共同或类似认知神经或行为效果的观点。更何况,目前有关镜像神经元和观察学习关系的研究结果也倾向支持上述结论。诸多影像研究显示“做中学”的操作活动所激活的镜像神经元竟然在纯粹的观察过程也表现出显著而稳定的激活,且其激活与操作活动中的激活模式和程度无异(Buccino & Riggio, 2006; Nyberg, Eriksson, Larsson, & Marklund, 2006),意味着“做中学”和观察学习具有相似,至少是共同的镜像神经机制。
如上所述,倘若观察学习与“做中学”确实具有一致或类似的神经功效,从神经教育学视角而言,这将意味着观察学习在教育中可能扮演着与“做中学”相似的角色,甚至更重要的角色。观察学习不仅可以直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其发生与结束较少受时间地点和情境的限制,观察者能随时随地在任何情境中进行观察学习。同时,观察学习在价值和道德教育领域也有着较“做中学”更显著的优势,这已是众多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所促成的共识。因为观察者发现示范者的某种行为反应获得负的强化结果时,他自己以后也会减少这种行为反应;相反,观察者发现示范者做出某种被社会道德规范禁止的行为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却得到酬赏,观察者就有将来做同类或类似负性行为的可能。当然,这凸显了观察学习中榜样或“靶子”之重要。除此之外,在“做中学”无法涉足的某些复杂行为领域,例如,无法容忍误差和尝试错误的载人航天或临床疾病诊断与治疗等教育实践领域,观察学习都可参与且是人们获取相关知识经验的重要方式。此外,观察学习还是创造性行为的重要来源。一般人们总以为,观察学习无非是“依样学样”或“依样画葫芦”,毫无创造性可言。实则不然,儿童或学生不只是从一个或一种示范榜样身上学习,他们往往从大量示范信息中获得不同内容,经过他们自己的认知加工就很可能会建构或产出新的观点与行为。即使给予相同的示范,他们也会从中各取所藉,获得不同的行为特征。因此,观察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学习者根据以前的经验和大量的示范信息重新组合的过程。重新组合不仅属于创造的一种类型或方式,而且其本身就包含着创造性的含义(蒋晓,1987)。因此,观察学习中所提供的示范信息量越大,种类越多、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行为反应。镜像神经元除了在联结和沟通观察学习与“做中学”中的重要作用,其对促进有效教学也有诸多启示。犹如陈巍等所指出的,镜像神经元研究有助于细化和超越静态和动态的教学示范设计之间的争论。镜像神经元的现有研究启示人们:动态视觉示范设计可能在涉及人类动作的学习任务中是最有效的(陈巍等,2010)。因为这种设计自动触发了由镜像神经元主导的具身模仿机制,进而以自动化方式启动了相似动作的执行。在该情况下,反对动态视觉呈现的原初理由——动态呈现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困难问题可能得以克服了。因此,动态视觉呈现对于观察诸如外科手术过程、手工装配任务、或者体育运动等学习任务时更有效,但在观察日常教学活动中自然物质(如,闪电或潮汐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或然性的抽象计算等教学中则可能无明显优势。
5. 结语
神经教育学仍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领域,它试图通过多层次和多途径来研究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建立心智、脑和教育的桥梁。神经教育学兴起的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和学习虽离不开手和身体,但主要是在脖子之上——大脑中进行的。换言之,脑是教育和学习的器官,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需更多地了解脑的结构、理解脑的工作规律,才有可能制订合理的教育政策,营造合适的教育环境,实现“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之教育目标。
方兴未艾的神经教育学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且逐步与人类的教育实践活动发生着深层的链接与互补互动。它为寻找一种适于脑的教育和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启示:它深刻昭示包括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决策和实施在内的各类教育工作者对脑(神经)科学甚至其他自然化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不可不知,对其理解和认识不宜简单化和庸俗化,更不可神话。就小学儿童教育而言,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当科学认识“关键期”与“潜能开发”的实在内涵,不为流传或鼓吹的“神经神话”所蒙蔽,对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所谓的具有时代变革性研究成果或者通俗世界奉之为圭臬的教育思想和原则应寻根溯源,并科学和敏锐地析辨它们“改头换面”后的变式,科学并人性化地促进儿童人格与素质健康地“成长”。正如朱小蔓(2005)教授所指出的,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脑。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培养脑和促进脑发展的过程。毫无疑问,各类教育工作者不应排斥或拒绝最新的脑(神经)科学或其他学科最新成果,应主动和积极地汲取其研究成果,科学和合理地引入和应用于儿童或小学生教育与培养实践之中,丰富和优化学生教育教学方式,促进和推动教学变革。就镜像神经元和观察学习关联性的研究成果而言,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对此类研究寻根探源及其前因后果条分缕析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将其引入到教育教学实践,倡导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根据镜像神经规律采用不同的教学设计和媒介策略,适宜得当地使用观察学习来替代“做中学”或其他教学方式,促使教育教学过程更加互动、开放和融洽,教学方式更富情境性和趣味性,使得学生能在学习过程中更自由和自主地表达与交流观点和思想,以及充分展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神经教育学对儿童教育实践甚至教育的启示不仅仅是某些来自实证研究的科学结论或干预规律,还涉及其学科中的思维方式、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等。例如,基于实证研究的理念正在影响各类教育理论及其教育实践(胡谊,桑标,2010)。德国马普研究所的重量级教授Stern就指出:“当前,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在制定决策时,尝试立足于实证证据,而不是观点、潮流或理念”(Stern, 2005)。这种循证(evidence-based)做法无不和神经教育学的理念完美契合。神经教育学所倡导的循证教育理念与文化不仅能够促进教育学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深层互动以及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群的交流和互惠合作(沈汪兵,刘昌,袁媛,2013),而且有助于缩短和消弭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距离,避免“思维在断裂处穿行”(叶澜,2001),优化和推动教育学学科及其学科群的发展。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神经教育学并不主张摒弃一切知识、情境和现象经验,“光秃秃”地从大脑层面来探讨教育和实施人类教化,它只是以一种开放和“超学科”方式为人们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视角,引导并倡导人们从多学科和多层面秉承循证思路来探讨和解析基因、环境、经验和进化诸多动力在刻画人脑和布施教化过程中的效用与作用机理。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SJB0649);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81029);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7KJB190002);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2018年校级教改课题。
文章引用
袁 媛. 神经教育学与儿童教育
Neuro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J]. 心理学进展, 2019, 09(07): 1203-1211.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7148
参考文献
- 1. 陈建翔, 陈建淼(2011). 镜像教育: 一个教育新主题的开始. 教育科学, 27(5), 25-28.
- 2. 陈巍, 汪寅(2013). 浊水上的桥梁: 镜像神经元与教育实践. 全球教育展望, 42(2), 74-85.
- 3. 陈巍, 张静, 陈喜丹, 丁峻(2010). 教育神经科学: 检验与超越教学争论的科学途径. 教育学报, 6(5), 83-88.
- 4. 单中惠(2002). “从做中学”新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3), 77-83.
- 5. 杜新, 陈天勇(2010). 老年执行功能的认知可塑性和神经可塑性. 心理科学进展, 18(9), 471-1480.
- 6. 胡晓琴, 傅根跃, 施臻彦(2009). 镜像神经元系统的研究回顾及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17(1), 118-125.
- 7. 胡谊, 桑标(2010). 教育神经科学: 探究人类认知与学习的一条整合式途径. 心理科学, 33(3), 514-520.
- 8. 蒋晓(1987). 略述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 外国教育动态, (2), 51-54.
- 9. 李萍(2012). 从教育神经科学理论视角解读中小学男生课堂问题行为. 教育与教学研究, 26(10), 8-11.
- 10. 李其维, 周永迪(2011). 教育神经科学: 一门极具实践意义和发展前景的新型学习科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 9(B6), 46-56.
- 11. 罗祖兵, 杨娥(2013). “过度学习”的危害及其救赎. 全球教育展望, 42(5), 26-34.
- 12. 乔文达, 董奇(2006). 神经神话与早期教育. 中国教育学刊, (5), 9-11.
- 13. 秦金亮(2008).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教育研究, (7), 59-63.
- 14. 沈汪兵, 刘昌, 袁媛(2013). 神经伦理学: 检验与僭越普遍与相对主义伦理的新进路.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5), 105-112.
- 15. 唐嘉忠, 王伟(2011).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前大脑损伤的研究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31(9), 1332-1334.
- 16. 王亚鹏, 董奇(2010). 基于脑的教育: 神经科学研究对教育的启示. 教育研究, (11), 42-46.
- 17. 吴永军(2012). 教育公平: 当今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 教育发展研究, (18), 1-6.
- 18. 杨元魁, 叶兆宁(2011). “做中学”对小学生同感能力发展的影响. 课程•教材•教法, 31(5), 82-86.
- 19. 叶澜(2001). 思维在断裂处穿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再寻找. 中国教育学刊, (4), 1-6.
- 20. 袁学松(2012). 神经教育学的发展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中国电力教育, (29), 1-7.
- 21. 袁媛, 刘昌, 沈汪兵(2012). 反馈相关负波与社会关系认知.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593-1603.
- 22. 周加仙(2009). 教育神经科学引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3. 周加仙(2010). 教育神经科学: 架起脑科学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桥梁. 全球教育展望, 39(4), 3-6+84.
- 24. 朱小蔓(2005). 道德学习与脑培养.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9(2), 8-11.
- 25. Anderson, M. L. (2010). Neural Reuse: A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the Br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 245-313.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10000853
- 26. Boyke, J., Driemeyer, J., Gaser, C., Buchel, C., & May, A. (2008). Training-Induced Brain Structure Changes in the Elderl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8, 7031-7035.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0742-08.2008
- 27. Bruer, J. T. (2002). Avoiding the Pediatrician’s Error: How Neuroscientists Can Help Educators (and Themselves). Nature Neuroscience, 5, 1031-1033. https://doi.org/10.1038/nn934
- 28. Buccino, G., & Riggio, L. (2006). The Role of Mirror Neuron System in Motor Learning. Kinesiology, 38, 5-15.
- 29. Elliott, D., Grierson, L. E. M., Hayes, S. J., & Lyons, J. (2011). Action Representations in Perception, Motor Control and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Medical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45, 119-131. https://doi.org/10.1111/j.1365-2923.2010.03851.x
- 30. Goldreich, D., & Kanics, I. M. (2003). Tactile Acuity Is Enhanced in Blindnes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3, 3439-3445.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23-08-03439.2003
- 31. Nyberg, L., Eriksson, J., Larsson, A., & Marklund, P. (2006). Learning by Doing versus Learning by Thinking: An fMRI Study of Motor and Mental Training. Neuropsychologia, 44, 711-71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05.08.006
- 32. Petrosini, L., Graziano, A., Mandolesi, L., Neri, P., Molinari, M., & Leggio, M. G. (2003). Watch How to Do It! New Advances in Learning by Observation. Brain Research Reviews, 42, 252-264. https://doi.org/10.1016/S0165-0173(03)00176-0
- 33. Rizzolatti, G., Fadiga, L., Gallese, V., & Fogassi, L. (1996).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3, 131-141. https://doi.org/10.1016/0926-6410(95)00038-0
- 34. Scholz, J., Klein, M. C., Behrens, T. E., & Johansen-Berg, H. (2009). Training Induces Changes in White-Matter Architecture. Nature Neuroscience, 12, 1370-1371. https://doi.org/10.1038/nn.2412
- 35. Stern, E. (2005). Pedagogy Meets Neuroscience. Science, 310, 745-74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21139
- 36. van Gog, T., Paas, F., Marcus, N., Ayres, P., & Sweller, J. (2009).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Observational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Dynamic Visualization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1, 21-30.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08-9094-3
- 37. van Schie, H. T., Mars, R. B., Coles, M. G. H., & Bekkering, H. (2004). Modulation of Activity in Medial Frontal and Motor Cortices during Error Observation. Nature Neuroscience, 7, 549-554. https://doi.org/10.1038/nn1239
- 38. Yu, R. J., & Zhou, X. L. (2006). Brain Responses to Outcomes of One’s Own and Other’s Performance in a Gambling Task. Neuroreport, 17, 1747-1751. https://doi.org/10.1097/01.wnr.0000239960.98813.50
NOTES
1笔者认为神经教育学较教育神经科学从字面上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其学科性质。严格意义上,educational neuroscience或者neuroeducation都是强调该学科的教育学涵义。尽管教育神经科学可能更多强调教育学的科学性,但也容易导致人们从中国短语“偏正结构”角度易误以为它更倾向于神经科学,相反,神经教育学从该中国短语语用学角度更易反映出该学科的教育学特性。
2诸如教育政策学等学科虽然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但由于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此不属“大”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