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Vol.
08
No.
04
(
2020
), Article ID:
37026
,
8
pages
10.12677/OJLS.2020.84073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王姿惠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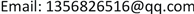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0年7月26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7日;发布日期:2020年8月14日

摘要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归属于应急法制,以知情权、危机管理为理论基础,内容涵盖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范围、途径等。我国现行适用于应急状态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未成体系,笼统概括、标准不明,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基础上,可从主体、标准、范围方面进行完善,推动统一的应急法制的建成。
关键词
信息公开,应急法制,知情权,危机管理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mergency
Zihui Wa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 26th, 2020; accepted: Aug. 7th, 2020; published: Aug. 14th, 2020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emergency state belongs to the emergency legal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right to know and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vers the principles, scope and way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mergency state.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emergency stat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hina are not systematic, general and unclear.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we can improve the main body, standard and scop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emergency legal system.
Keywords:Information Disclosure, Emergency Law, Right to Know, Crisis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0年春季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优越性,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和以医护人员为首的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但不可否认,在整个过程中集中暴露了现有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缺陷。2019年12月初,武汉市已经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从12月8日官方报告第一例病例至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教授在电视直播采访中首次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中间50天的时间,政府官方没有及时公开与疫情有关的关键信息,更没有发布预警信息。期间,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强调“未发现人传人现象”,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对社会层面出现的预警信息进行了治安管理处置,2020年1月3日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对李文亮医生进行训诫。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了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措施。至此,本次疫情正式纳入应急法制调整范围。
疫情信息公开属于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部分。我国应急法制发展起步晚,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关于应急状态政府信息公开无专门立法,现有规定十分有限,且在公开主体、公开范围、重要标准界定等方面存在问题,急需从立法上加以修正,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2.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般法理
2.1. 相关概念界定
1)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以法定形式并通过法定程序,主动或依申请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个人、组织公开的制度 [1]。应急状态下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同于常态管理下的政府信息公开。为适应应急状态需要,信息公开主体更为多元,不仅仅限于行政主体;范围更为广泛,既包括常态管理下行政性内容,也包括与应急状态有关的事实信息、公民个人信息等。
2) 应急法制与突发事件
应急法制,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针对突发事件及其引起的紧急情况制定或认可的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成。它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在应急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 [2]。本文所研究的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属于应急法制体系。
应急法制中的核心要素是突发事件,因此,对突发事件的界定将直接决定应急法制调整的范围。我国突发事件的概念规定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具有发生突然性、事件复杂性、影响持续性、危害严重性。为更有效地采取措施,有必要对突发事件进行分类与分级。最常用分类的是根据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将其划分为人为性突发事件与自然性突发事件 [3]。我国立法综合其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2.2.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依据
1) 知情权理论
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 [4]。从其产生来看,知情权与人类文明、民主政治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西方世界代议制民主的确立,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而政府信息的获得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的前提。同时,知情权的确认也有利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履行义务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在第四十一条规定赋予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尽管《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我国学界和立法并没有忽视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有标志性意义。在应急状态下,知情权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此时大部分的关键信息往往由政府掌握,而这部分信息的公开与否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健康及财产权利。基于此,政府应及时、准确、客观的公开有关信息。
2) 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是组织对危机的预测分析、防范和应对,涵盖了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上世纪60年代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两国意识到核对抗的危险,危机管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推动了我国学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危机管理可分为企业危机管理和公共组织危机管理,本文所指的是公共组织危机管理。该理论认为信息沟通在危机管理中有重要意义,尽管在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中为有效沟通而进行的信息公开将造成引起部分社会群体的恐慌,但及时的沟通将有效防止信息的误传和谣言的散布,安稳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信息沟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日益缩小,但政府依然需要警惕消极的虚假言论。另外,非典型肺炎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等近些年发生的危机事件警示我们仅仅靠政府或国家机关的力量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共度难关。
2.3.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原则、范围及途径
1)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原则
世界上多数国家政府信息公开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指导思想,应急状态下政府的信息公开更加应当遵循。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较为充分,言论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应急状态下信息公开上实际完成度较高。但在我国,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相对严重,政府通常能获得丰富的信息,而普通民众的信息相对匮乏。且存在数量众多的领导干部没有破除传统的行政思维,将人民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信息的公开往往“报喜不报忧”, 甚至利用不平等的地位控制大众媒体对新闻的报道。因此笔者认为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明确“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标准和理念。
2)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范围
基于“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标准和理念,笔者认为应当仅以列举方式说明不得公开的事项,换言之,除保证常态管理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范围外,就个别事项根据应急状态做特殊处理。
3)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途径
在信息公开的途径问题上,考虑到突发事件具有发生突然性、事件复杂性、影响持续性、危害严重性的特征,应选择更加及时、便捷、全面的传播途径。例如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我国政府将疫情和患者信息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途径及时向社会大众公开,为人民采取预防保护措施提供了更多机会。当然,这有赖于科研、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传递方式的不断革新。但值得肯定,大众传媒在应急状态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3. 我国应急状态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问题分析
我国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现状应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应急法制分别考察(见表1、表2)。
Table 1. A study on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China
表1.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考察
Table 2. A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emergency legal system in China
表2. 我国应急法制相关立法考察
3.1.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未形成统一体系
如前文所述,我国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散见于众多法律、法规之中。在应急状态法律规范方面,主要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结合《防震减灾法》、《防洪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等单行的法律法规形成了应急法制体系。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方面,仅有一部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没有法律位阶更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
目前来看,现有格局下应急状态政府信息公开未形成统一体系。应急状态法律规范除《突发事件应对法》外,均为针对某一单一灾害、事件或疾病,如《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等,其中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并且存在同一问题规定相互矛盾、不一致的情况。而常态管理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程序相对繁杂,且部分内容根本上不能在应急状态下适用。如,常态管理下“谁制作、谁保存、谁公开”的规则, 为应急状态信息统一发布所取代。
3.2.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体设定不合理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直接针对应急状态的立法,根据该法,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都有责任在其行政区域内向公众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但突发事件是一个庞大而笼统的概念,法律明确进行分类、分级后,并没有按不同分类、分级规定不同的信息公开主体。
这使得在应急状态下,信息公开主体的确定依然遵循不同类别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由此暴露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这些法律、法规确定的信息公开主体通常适用于常态管理,而不适应应急状态政府信息公开的现实需要。该问题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尤为突出,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赋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传染病爆发或流行时公开或授权省一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开其行政区域内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权利。尽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言明适用情形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但试问,在应急状态下,将信息传递到有权向社会公布的最低一级行政主体——省一级政府需要多长时间?通过多少流程?更不必谈信息何时到达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了。应急状态非正常状态,没有充足的时间层层上报,逐级审批,“应急”的关键在于“急”,信息公开主体设定的不合理浪费了全社会积极应对的宝贵时间,往往使形势恶化甚至失控。
再者,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内法律、法律规定存在相互不一致的现象,而当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产生矛盾时,简单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使责任主体之间互相推诿,各级政府领导为自身政治利益在不同的信息公开主体规定面前选择“就高不就低” [5]。如上述《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设计,县级以上省级以下政府根本难以实现对其行政区域内突发传染病情况的信息公开。
3.3.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要标准不明确
目前的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信息公开范围、时间、方式、程序等规定不明的问题,法律、法规只规定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公布信息,而具体公开那些信息,什么时间公开,以什么方式公开,遵循什么程序,没有明确的标准。政府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一些地方政府仅仅是极为有限的公开甚至不公开。
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发布不同级别警报后,“定时”公布与公众有关信息,“及时”发布警告、建议、劝告。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是该法中为数不多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而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应有效果。对“定时”和“及时”的理解,不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无独有偶,《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亦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的时间标准采用了“及时”一词。此外,适用该条文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确认出现了“传染病”,否则便不存在“传染病疫情信息”,也谈不上信息发布。而该法对于逻辑链条中的关键因素“传染病”仅做了列举,并没有明确传染病的法定概念以及辨别传染病的标准。现实是,应急状态中出现的疾病很多为非法定传染病,即不明原因疾病,从法律角度讲,很难通过应急法制向社会公开。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作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但涉及应急状态的规定,亦存在标准不明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均为一大难题,而“重大影响”也难以判断,毕竟在应急状态下,事件是复杂的,影响是必然的。
3.4.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预防性信息缺失
尽数阅读我国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有关法律、法规,绝大多数条文的规定为既有事实、调查研究结果的公开,只有《防震减灾法》第三章的地震监测预报涉及了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预防性信息公开。其问题在于,应急状态下,对某一突发事件的分析进而得出确定的结论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在此过程中信息公开的缺失极有可能失去控制态势的最佳时机。再者,若把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放在信息的过分精确、全面上,那么显然不能实现应急状态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例如,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出现早期,官方通报均为“未发现人传人现象”,这使全社会放松了对不明原因疾病的警惕心,一切聚集性活动照常进行。倘若当时通报内容为“发现不明原因疾病,不排除存在传染性的可能”,效果一定更优。当然,质疑在于,预防性公开是否会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危及社会秩序。笔者认为,首先,生命健康权至上,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及时通报所有事关公民生命安全利益的信息。其次,危机沟通的要点在于沟通,隐瞒不报势必将扩大危机,信息透明反而可以减少社会不安情绪。
4. 完善我国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措施
4.1. 建立统一的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建立我国的应急状态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应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对现行应急法律规范进行集中清理和修改,尤其注意解决同一问题不同规定相互矛盾、不一致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紧促成《紧急状态法》的颁布。
在此基础上将现有的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与常态管理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建立规范、完整、可操作性强、适于应急状态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尤其在公开主体、申请与公开方式、公开程序方面做出有益调整。
最后,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及该体系下《紧急状态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在条件成熟时,应明确将“保护公民应急状态下的知情权及生命财产安全等”作为立法目的写入正文,借以弥补目前我国宪法未将知情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和其他部门法未对公民知情权保护做明确规定的空缺。
4.2. 适当放宽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限制
首先,从立法上将应急法制中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层级下调。例如,消除原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县级以上政府”行使政府信息公开权力的制度障碍。为应对未知的应急情况,立法应对例外作一定程度的保留。
其次,赋予掌握信息的专业人员信息公开的权利。如前文所述,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的概念不同于常态管理下行政性的政府信息。多部现行的法律规则,都规定了专业人员的报告义务。如,《防震减灾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研究所得的地震预测意见,应当向有关机构、地方政府和国务院中的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同时在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将专业人员对地震预测意见的公开范围限定于本人或者本单位对长期、中期地震活动趋势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进行相关学术交流。《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条规定,医疗、疾控机构及其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疫情报告原则、规则进行报告。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确诊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有报告的义务。但上述立法均限制专业人员公开信息,甚至是明令禁止。从应急状态下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讲,应当有条件的赋予专业人员发布信息的权利。且专业人员往往掌握的是大量事实信息,以医疗机构及人员举例,其所掌握的几乎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病例、有哪些临床病症、是否是新型疾病等,这些信息的发布必然不同于谣言的传播,并不会引起巨大的负面效果。
最后,社会大众及媒体的信息发布权利也不应该全部被剥夺。应急状态下,事发当地的人民、与有关人员密切接触者、接到群众线索的媒体等都可能收到政府掌握或隐瞒的各类信息。社会大众基于事实所发布在社交平台的信息、媒体发布在其线上线下载体上的真实新闻报道应得到保护。由此可形成竞争性公开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部门积极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责。
4.3. 严格明确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重要标准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众多不确定因素严重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急需严格明确。
第一,时间标准。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开条例》为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间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开条例》虽然未提及明确的信息对外公开时间标准,但对内的信息报告有具体的标准,规定在第十九条、二十条,以“1小时”、“2小时”明确了《传染病防治法》报告制度中的“及时”标准。笔者认为,政府信息对外公开也应当有明确的时间标准,真正达到“及时”的要求。该时间标准的设定不可直接照搬《突发卫生事件公开条例》的“1小时”、“2小时”,公开信息所需的时间显然较之在内部系统中上报更长,应在保证结论信息已经充分调查研究前提下尽可能缩短时间,具体需要立法和相关部门结合众多事件的经验及实际情况确定。从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总体立法上规定最低时间标准,具体到不同类别的突发事件,可根据其特殊性通过行政法规等形式进一步规定。
第二,关于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暴露的“传染病”法定概念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政府信息公开的延误体现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中规则层面的致命缺陷——仅以法定方式列举并分类明显不足以“应急”。因此,应尽快明确“传染病”的法定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以应对不明原因疾病的不时出现。否则应对不明原因疾病引起的诸多问题将根本无法适用现有的传染病应急法制 [6]。
4.4. 在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增添预防性信息
传统思维模式下,往往将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效果设定在“控”字上,即控制已发生的突发事件及引起的紧急情况,忽略了“防”的重要性,低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相比被动的应对、处理应急状态下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更应该追求主动预防,未雨绸缪,化解或尽可能降低风险。突发事件具有发生突然性,但其不可预测并非绝对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通过先进的设备和方法将越来越准确的预估其发生的可能性。综上,从可行性及重要性角度讲,建议在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增添预防性信息公开的部分。
第一,从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总体立法上规定政府应在一定合理时间内公开其在突发事件发生前或早期获得的有关真实信息,即使此类信息仍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此类信息由于具有有待进一步分析的特殊性,其公开范围可仅限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可能受此影响的地区。第二,在没有充分证据前,禁止发布排除危机发生可能性的信息。第三,政府应联合相关领域专业人员为可能到来的应急状态向社会公众提供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危机的科学指导。例如,在疫情可能发生时,根据现有资料,通知公民注意佩戴口罩,避免拥挤人群等。
5. 结语
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结束后,我国从中吸取教训,加强了应急法制的立法。但受现实情况和立法水平限制,众多规则缺陷使我国在应对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再次错失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防控工作处于被动。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深刻反思疫情中体现的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及整个应急法制的问题,结合国外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国情,以常态法立法水平和完备程度对我国应急状态下法律规范作全面的清理和修正,形成统一的应急状态法律体系,从根本上满足应急状态下“应急”的需要。
此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必须实现传统行政思维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尤其在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应以保护公民知情权、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权利为重。推诿责任、隐瞒问题,不仅仅是制度的缺陷,更是政府不作为的表现,现状不加以改变,必将大大削弱政府公信力,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从长远来看,本文期望从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入手,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治理体系改进,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应急状态下的领导力、组织力,不负其职责和人民的期待。
基金项目
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0159)。
文章引用
王姿惠. 应急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mergency[J]. 法学, 2020, 08(04): 516-52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4073
参考文献
- 1. 刘恒, 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
- 2. 韩大元, 莫于川. 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7.
- 3. 李栋, 周静茹. 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置实务[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8.
- 4. 汪习根, 陈焱光. 论知情权[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2): 62.
- 5. 沈岿. 传染病防控信息发布的法律检讨[DB\OL]. 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13613, 2020-3-17.
- 6. 王锡锌.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克服[J]. 法学, .2020(3):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