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Vol.
09
No.
02
(
2021
), Article ID:
43334
,
6
pages
10.12677/JC.2021.92006
浅析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之异同
刘润泽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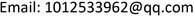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0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16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23日

摘要
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从它初登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直至今日,“女权”更是成为了遍布全球社会各界以及众多社交媒体的热词。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女性主义运动接连出现新的浪潮,这也启发了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影视导演,逐渐将女性主义思潮融入自己的影视作品创作内涵之中,为女性主义影视发展史不断添砖加瓦。本文试以对比研究的方式,来分析中外当代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的异同。
关键词
中外比较,女性主义,影视作品
An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Foreign Feminist Films and TV Works
Runze Liu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May 20th, 2021; accepted: Jun. 16th, 2021; published: Jun. 23rd, 2021

ABSTRACT
Womanism, or feminism, has kept its vitality from the moment it first appeared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Until today, “feminism” has become a buzzwor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any social media. Not only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changes, new waves of feminist movement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s also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 and television directors around the world to gradually integrate feminist ideas into the creative connotation of their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China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y of feminist film and televisio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by wa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Keywords: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rison, Feminism,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于西方,在197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的《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中有所涉及。它粗略的认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但宣言者在当时的父系社会下很快就被人推下了人生的断崖。尽管如此,女性主义却已经作为一个在理论和逻辑中“应该有”的抽象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同时由于19世纪末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化,加之三次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女性主义也逐渐从最初的无稽之谈演变成了众人拥护的信条,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这一主张也逐渐成形并受到社会上愈来愈多人的认可,在此浪潮的冲击之下,西方诸多影视导演逐渐将视角转向女性,西方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也开始陆续登上历史舞台,来展现并映射当时西方社会的大背景。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发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妇女在国家的支持下实现了社会和经济解放。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被评为第一个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旨在赋予中国家庭妇女政治、社会、教育和财政资源 [1]。“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其主题在概念和语言上都出现了不小的争议,因这一概念经历了从西方传播到日本,再由日本传播到中国这一复杂的过程,导致上世纪中国妇女学学界一直无法确定是用“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来翻译feminism,直到1994年,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最终决定将feminism翻译成“女性主义”。而在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上,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无论在起步还是发展阶段都晚于前者,且二者在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异同之处。
2. 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的相似性
2.1. 隐喻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西方女性一直处于亚文化地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二者在女性主义影视作品表达之中必然存在相似之处。无论是《圣经》中肋骨的设定,还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女子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均被视为男子的附庸,处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地位的最底层。这种观念作为文化基础,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构建,同时又反作用于女性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构建,形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但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妇女意识逐渐觉醒,妇女解放运动也随之兴起,争取男女平权,唤醒女性自由独立意识逐渐成为女性革命的利刃。1993年由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执导的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是西方早期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影片的核心色彩蓝取自法国国旗的三色之一,其代表象征着自由,且着重强调着女性对独立意识的向往与追求。在影片的开场,女主人公朱莉就因一场车祸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以及女儿,这在那个身处男性力量有形主宰与暗中掌控的父系社会,朱莉可以说是失去了自己的所有依靠以及生存的意义,导演也确实在影片的前半段展现了朱莉身上具有的旧时期传统女性的特点,她无法接受作为自己全部女性依靠的丈夫以及家庭的死亡与覆灭,她无法摆脱女性固有的他者身份,即使这种身份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男性或者说男权社会强加的、虚无的,这些表达充分体现了导演对女性独立人格转变过程中的深切思考与感悟,她以社会中更真实、更令人接受的叙事方式来表现着女性主义。在朱莉轻生未果逐渐康复并与过去做了彻底的清算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寻找新的生命意义,开启一段新的人生篇章,这些细节也都充分体现了电影中女性自由独立思想的萌发,对于朱莉,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它也只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像朱莉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上心头。朱莉受骗的感觉使她改变如此之大,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她想过的日子。那即是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感觉中解脱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爱是一种牢狱吗,抑或是种自由?” [2] 在朱莉最终知道丈夫早已出轨的消息后,她卸下了自己所有的负担与防备,宽恕了能宽恕的一切,给予她人自己的剩下的所有,完成了丈夫最后的乐章,以一个独立自由女性的身份去拥抱了自己的幸福,得到解脱,重获新生。
在中国,2006年由导演宁瀛执导的电影《无穷动》同样暗喻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影片中妞妞因查找丈夫情人的背景召集姐妹们来到家里,女人们聚集起来无所不谈,其中涉及各自的性体验,借助“性”夺取女性话语权,如同是在对父权下女性失语状态的挑战。性别视线突破了欲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看的快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穆尔维提出的“反快感”观看模式。另外,影片通过特写镜头刻画出女性身体、面部出现的衰老,希望借助女性身体之丑来影响男性对女性的“观看” [3]。这里的女性不再是推动叙事的牺牲工具,也不再是男性的审美工具。当男性的缺席与女性的在场形成对比,当传统影像中的性别构建方式被颠覆,影片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实现了女性地位的隐性提升。
2.2. 尝试打破固有的性别束缚
在西方,随着工业化进程,大量男性外出工作,女性负责照料家务,所以家庭和家庭以外的领域被自然划分为私人和公共领域。再看中国周礼第一次以条文的形式对两性的活动空间和工作范围进行了重新规范,将社会与家庭工作范围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这样的性别空间划分几乎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使得妇女基本无从获得事业和社会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像是无形的枷锁桎梏着女性,使女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父系社会的牺牲品,逐渐导致两性身份及关系在社会中的失衡,而在中西方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都体现出打破这一现状的尝试与表达。
正如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的观点,“妇女的‘本质’更像是三角的本质,而不是像‘内在于自身’的本质:正是明确的身体特性(如一个女性具有女性性征的身体)、性格素质(提供爱与关怀的气质、与身体的某种关系等)或作为妇女的必要属性(如女性化的经验、作为女性在世上生活的经验),即妇女在其不同的父权制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或者历史地受到束缚的特性” [4]。在西方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朱莉作为一名女性、妻子、母亲,一个弱者,她本应在各种受限的处境中做出选择,努力去界定这种三角关系的可行范围,而也正是由于她需要的、努力想要达成的这一三角关系,对内以一种传统观念的形式禁锢并束缚着女性的思想灵魂,对外又以一种固有身份制约并主导着女性的行为权力,使得她追求自由的道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在车祸将这一切都改变了之后,朱莉作为女性虽然从客观事实上摆脱了其在男权社会中的沉重镣铐,但她在主观精神上却仍然依附于这种三角的本质,这种主客观的极不统一,也导致其逐渐崩溃,甚至一度尝试滥用药物去了解自己的生命。《第二性》著作者波伏娃指出,女性之所以受压迫,其源于女性的她者性质以及在父系社会的边缘性与从属性地位 [5]。凯特·米利特也在《性的政治》中则倡议将传统上与男性相联系的刚强勇毅和传统上与女性相联系的同情悲悯结合在一起,如此造就理想的人 [6]。在电影中,在朱莉这位女性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她如男性一般少言寡语、直截了当的做事态度,同样她也表现着女性淑质英才、心慈好善的优良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男女在性别上的结合与统一,且她拼尽全力以一种独立自持的主体身份,在内部自我思想解放与外部社会身份转变的统一体系中寻找女性自身的存在价值、生命意义,为打破固有的女性性别束缚甚至促进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发展都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
而在中国电影《送我上青云》中,导演用质疑性别话语体系的解构方式力图突破两性对立的二元框架,他将女主人公盛男塑造成了花木兰式的人物, 即女性身上存在着男性的特质,而记者的职业标志着她性格特质上的打抱不平,以及不修边幅的外貌,用去女性化的方式开启了找寻的开始 [7]。影片借用对“女性如何在的家庭伦理身份和社会伦理身份之间达到平衡”这一问题的探讨,试图打破女性在社会中的性别束缚以及墨守成规的性别空间,但结果却不容乐观,盛男在职场之中虽获得了自己的社会性别,但却失去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和职业相对应的要求是女性形象的中性化,这又与富有女性特质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失败形成了对比,家庭与职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性别悖论,即生理特征和社会特征在现代女性身上难以并存。
3. 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的差异性
由于女性主义是西方舶来文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进行得热烈时,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同时,东西方文化本身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中西方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又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第一,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上。1993年由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执导的西方女性主义电影《钢琴课》中的爱达,1987年由导演黄蜀芹指导的中国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中的秋芸,她们都属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女性形象,在两部作品中虽都表现了女性的抗争,但二者的表现方式却截然不同。艾达在面对父权与夫权的压迫时采取的是一种女性化的抗议方式,而秋芸采取的是一种男性化的抗议形式,正如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所说:“如果她想充分成为女人,这就意味着她要尽可能去接触男性。女人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与男人平起平坐,必须要有进入男人的世界的途径。” [5] 爱达与秋芸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进入男人世界的途径,爱达穿着一身优雅的长裙,盘着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发髻,举手投足间散发出强烈的女性魅力,而秋芸则是一头短发,身着短裤和背心,男性化的装扮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她采取男性化的行动与男性化的语言,力图摆脱男性的奴役。她的这种抗议方式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年幼时的秋芸亲眼看见母亲出轨的场面,让她产生对于母亲的憎恨,她开始拒绝成为女人;二是她对于戏剧舞台的热爱,为了实现扮演钟馗的舞台梦想,女扮男装可以说服父亲让自己继续留在舞台,而剧团张老师对她扮演武生的肯定也是她继续以男性装扮示人的重要动力,但秋芸内在的自我认同仍是一个女人,她很排斥剧团的伙伴叫她“假小子”,当发现自己爱上张老师的时候,秋芸也试图改变扮相,还原自己的女性形象。而为了在男权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秋芸还是选择继续采用男性化的抗议方式,她的这种选择也就是李银河在《两性关系》中所提到的一种跨越性别现象:“认为人有可能表面做一种性格,但心里认同是另一种性别。” [8] 秋芸暂时放弃自己的女性气质,其实是她的一种生存“策略”。她以男性化的装扮“乔装”进入男性世界,为的是获得社会对她女性身份的认同,这种男性化的抗议成功地让秋芸完成对女性自我身份的重构,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而艾达的选择就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男人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个体,与男性平等。” [5] 因此爱达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没有拒绝女性属性,且她凭借无可抵挡的女性魅力征服了两位男性。爱达的反抗并不依赖与男性形象的趋同化,而是用失语的方式将内在心理展现出来。她借助如泣如诉的琴声来表达着内心极度的不满,用坚定的行动控诉着男权社会。女人和男人尽管有着生理上的差异,但女性也应该有平等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去努力摆脱由身体和精神上束缚。相比秋芸激烈男性化的抗争形式,爱达的抗争显得更加的柔和与细腻,但这种抗争带给人的震撼更具力量。
第二,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的文化视角上。西方电影《钢琴课》的导演简·坎皮恩出身于一个艺术之家,父母都是舞台演员。她习惯运用细腻与圆润的手法表现女性内心的感触,不动声色与含蓄地传达出爱达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简·坎皮恩以极度的感性来探讨西方女性的觉醒,去关心女性内心的成长,深入受压抑的妇女的精神世界,在爱达这一人物塑造上,既可以体现西方所强调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饱含理想主义气息。电影中通过对男性身体的窥视镜头就已经打破了传统,体现着爱达作为女性对异性身体的渴求,此时爱达已经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她是手握选择权的那个人,而两位男性成为了他者,且爱达最终的选择究其本质其实是为了自己喜爱的钢琴与音乐,这些东西代表了她的个人价值与追求,可以说导演在其中所展现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女性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影片《人鬼情》中秋芸是导演黄蜀芹的自我映射的一个人物形象。出身在中国一个艺术世家的黄蜀芹从小就怀着艺术的梦想,在她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文革的到来让她的父母遭遇迫害,丧母的痛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梦想,并决定将自己的镜头转向女性这个边缘化的群体 [7]。秋芸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创作者希望通过以男性的规范为标准,让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站在男性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从而实现平等的观念。黄蜀芹希望通过镜头来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秋芸这一女性形象塑造体现的更多是一种集体主义,同时充满了现实主义气息。尽管她的反抗和呐喊是微弱的,但是毕竟跨出了中国女性建构自我主体的第一步,为其他女性指明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道路,体现出导演强烈的女性意识。
第三,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中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创作中。2011年由郑晓龙执导的清装宫斗剧《甄嬛传》等同样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将女性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误解了其真正的含义与本质。看似以女性为叙事的中心,但实则还是在以皇帝即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系社会中谋求女性的生存及发展。汉娜·阿伦特曾说,权力得以维系需要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暴力,二是公众默认,而公众默认比暴力的作用更隐蔽和持久 [9]。而在《甄嬛传》中妃子(女性)对皇帝(男性)无条件的服从与讨好,恰好完美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统治的默认与惯性的容忍,这就更加加剧了男性对于女性的专制统治,使两性关系的严重失衡与异化成了理所当然。且《甄嬛传》建构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性绝对服从与男性并失去反抗意识的世界,女性无论在内在的心灵思想还是外在的行为权力,都完全束缚于皇帝的既定要求与自我喜好,女性已经被物化,成为他者与客体,失去了女性真正的生存目的与意义。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父系社会“建构”成的。这种“建构”依赖于传统社会的两性观念,作为社会观念为载体的影视作品中被反复强化的女性形象,是男性依照自我理想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甄嬛传》中,所有的妃子乃至宫女,个个都是依照男性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物件”,她们无一例外的拥有着美丽动人的脸颊、身材姣好的外形、百依百顺千娇百媚的性情,这完全就是“机械复制时代”下的产物,在这过程中女性的内心变化与人物关系也不过只是一种站在“伪女性”立场上对父系社会框架的重申,这的确与女性主义最初的主张与追求南辕北辙,但也为后续中国女性主义影视作品创作起到了一定的警示意义。如2016年由王一淳自编自导的犯罪类型青春影片,2017年文晏执导的剧情片《嘉年华》等社会主义新时代影视作品,都在吸取经验之后,随即将中国女性主义电影创作的中心转向了青春期女性的成长历程这一主题,在《黑处有什么》电影中,女孩成长中出现的生理期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电影符号反复出现,随着女孩身体的成长,生理期作为一种标志,一种女性区别于男性而自身独有的特征,它象征着“女孩”到“女性”的转变,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初潮”标志了女孩由孩童时代正式迈进成人世界,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意识、性别意识萌发与觉醒的象征。随着曲靖的进一步成长,她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的好奇心,开始驱使她去探索那些被传统父系社会建构的、作为女性禁忌的“黑处”,这暗含着女性对男性世界决定性与权威性的质询与挑战,利用青春期少女的懵懂纯洁视角去摸索观察成人社会的黑暗污浊现实,从而产生巨大的反差,通过这种对立表达出新时代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而在电影《嘉年华》中,同样体现了女孩到女性的意识觉醒、对父权社会的挑战、作为女性主观自我主体对自身、社会的独立判断及自我成长,这也足可看到中国女性主义的不断进步与自我完善。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中西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既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在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中亦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女性的固有偏见仍然无法完全消弭,女性主义理想的实现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但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从开始的只是片面地反映女性的情感世界、生活经历、性别体验等浅层方面,逐渐发展为真正的以女性的视角,切实的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反应他们的内在与外在,去表现他们的矛盾、妥协、抗争与思考,以真实的方式去反映特定年代特殊环境中的各种不同女性的共同需要、现实境遇中女性所遭遇的最敏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女性自我对性别意识的识别、女性的自救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触动和精神对话等等,透过女性主义及其影视作品的不断成熟,足可见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前进。
文章引用
刘润泽. 浅析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影视作品之异同
An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Foreign Feminist Films and TV Works[J]. 新闻传播科学, 2021, 09(02): 32-37. https://doi.org/10.12677/JC.2021.92006
参考文献
- 1. 陆希. 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思辨[J]. 检察风云, 2019(5): 16-17.
- 2. 周星宇, 袁智忠.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伦理——以《蓝》《白》《红》三部曲为例[J]. 文化与传播, 2019, 8(4): 76-80.
- 3. 纪莉, 王燕灵. 对抗性“凝视”中的“他者”——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电影的反“凝视” [J]. 当代电影, 2020(6): 141-145.
- 4.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艾晓明,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5.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郑克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6. [美]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M]. 钟良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7. 王聆懿. 中国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困境的嬗变——以《人•鬼•情》《杜拉拉升职记》《送我上青云》为例[J]. 中国电影市场, 2021(2): 47-50.
- 8. 李银河. 两性关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9. 张黎呐. 《甄嬛传》的“伪女性”叙事及宫斗剧的价值观异化[J]. 创作与评论, 2014(2): 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