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08
No.
04
(
2019
), Article ID:
29713
,
8
pages
10.12677/ASS.2019.84070
The Shaping of Yin Changheng and Sichuan Military Government's Legitimacy
Bao W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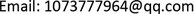
Received: Mar. 25th, 2019; accepted: Apr. 8th, 2019; published: Apr. 15th, 2019

ABSTRACT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Zhao Erfeng, who was then the Governor of Sichuan Province, was forced by the situation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and handed over the regime to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led b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owever,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t this time is not stable and faces difficult problems.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Government. Yin Changheng, then the governor of Sichuan, successfully shap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regime by strengthening Zhao Erfeng’s negative image, demonstrating the legitimacy of his revolution, and creating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new government. It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Southwest region and the country’s border security.
Keywords:Yin Changheng, Sichuan Military Government, Legitimacy
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合法性的塑造
王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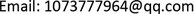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9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19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19年4月15日

摘 要
武昌起义之后,时任川督的赵尔丰迫于形势,宣布独立,并把政权交给革命党领导的军政府。但此时的军政府根基并不稳固,面临着种种棘手的难题。在此种情况下,彰显新政府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通过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以及打造新政府的政治认同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地塑造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国家的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尹昌衡,四川军政府,合法性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政权合法性,即统治的正当性,也就是“一个政权或一种政治权力被相信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获得人们自愿服从或认可的属性和能力” [1]。任何政权都会极力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如韦伯所说:“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 [2]。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纷起响应。时任川督的赵尔丰迫于形势,宣布独立,并把政权交给以蒲殿俊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但此时的军政府根基并不稳固。由于未能成功地安抚巡防军,遂酿成“成都兵变”。时任军政府军政部长的尹昌衡力挽狂澜,平定叛乱,并在各方力量的推举之下出任军政府都督 [3]。新成立的军政府在极为复杂的局面中,面临种种棘手的难题。在此种情况下,彰显新政府的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尹昌衡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军政府的合法性。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军政府的统治,更为川渝统一奠定了基础,并对稳定整个西南地区的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2. 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
旧政权的“失道”,是新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而对旧政权代言人的抨击,即是对旧政权合法性的最大破坏。赵尔丰作为晚清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自然不免成为抨击的对象。通过对赵尔丰负面形象的强化,进而实现攻击晚清和树立新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图。
首先是强化赵尔丰在保路运动中“屠夫”的形象。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断然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了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很快发展成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各省群众相继集会,游行示威,而且罢工、罢市、罢课,拒交租税,并成立了保路团体。其中以四川人民的斗争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接着各府、州、县相继建立了分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到了8月,斗争浪潮推向高峰,成都人民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继续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则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根据清政府“切实镇压保路运动”的指示,首先诱捕了四川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成员,接着突击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当天下午,成群的市民涌到总督府,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人。赵尔丰突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群众当场被打死32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即震惊一时的成都血案 [4]。有学者通过对“通饬札”的解读,认为赵尔丰是希望通过“中正平和”的方式平息朝廷和川人之间“路权”的争端。作为地方官的赵尔丰比朝廷更了解四川的民情和保路的缘由,他之所以多次向清廷陈诉川人修路的原委,反映川民的诉求,请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是因为他深知贸然强制推行不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铁路国有”政策,极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乃至危及清廷的统治 [5]。但成都血案的发生,总归是与赵尔丰有关联。故尹昌衡在发布军政府成立通告中历数赵尔丰的罪行:
“查成都自七月十五逮治为首争路抗捐诸人,并督署枪毙市民之后,激成众愤,川西南同志军纷起问罪。赵尔丰不知自反,竟派兵四出剿杀,众情益愤,愈剿愈甚,苦战者七八十日,糜烂者数十州县。以血肉之躯,与快枪利炮相薄[搏],死伤丧亡,尤难缕述。至九十月之交,同志军战久疲惫,赵尔丰督战愈急,骎骎乎有民不敌兵之势。且是时重庆组织独立事机已熟,钮传善连电告急,尔丰方拟乘其未定,督师东下。又探闻南北军聚于武汉,战事方殷,胜负未ト。当是时也,对于外非独立无以应事机,对于内非独立无以全民命。然赵尔丰身拥重兵,驻省城者不下万人,而横残之田征葵所辖防军,实居多数。民党手无寸铁,虽屡谋冒险举事,而障碍多端,细审事势,亦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非徒无益,且滋民害,乃不得已而求和平之解决” [6]。同时,尹昌衡在其《自记》中亦说:“尔丰固刚愎,诈殿俊等十九人入署议,皆捕之。四民号泣,咸戴德宗主环督署而吁,哀声动天地。尔丰怒,发巨炮击之,洞胸折股者数十百人。尸于市,民益汹汹。郊野闻之,扶老携幼……尔丰恚甚,诬为叛,纵兵屠之。浮尸十里,闾舍荡然 [7] ”。
通过对赵尔丰“屠夫”形象的宣传与强化,从而树立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和军政府的合法性。
其次是强化赵尔丰在“成都兵变”中的“幕后”形象。“成都兵变”主要是指1911年军政府因军饷发放问题而引发的士兵哗变。军政府原宣布发饷三个月,结果却只发了一个月饷,有人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放饷委员,接着兵变发生,整个成都一片混乱。首先是抢劫银库,跟着各典当铺、大商店、公馆、以至于居民富户都成了洗劫对象,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早已在混乱中逃走。尹昌衡此际挺身与凤凰山标统周骏一同率兵进城,一面派兵看守军械库,防止武器被抢,一面派亲信军官收容散兵游勇,兵变逐渐被平息。而关于赵尔丰是否是“成都兵变”的幕后黑手,学界大多否认赵尔丰为“成都兵变”的制造者,这里不做赘述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报纸报道与军政府官报以及尹昌衡自记有所出入。军政府在给《民立报》的文告中说:
“清总督赵尔丰,知满清大势已去,率其所属,拱手退让。即以赵尔丰之反复叵測,七月十五、十月十八两次为逆,害我川民,亦不过将尔丰及其党中之罪恶彰著者诛速数人,余者毫不株连” [8]。
在给《申报》的文告中说:
“都督示云:十八之变,赵逆作俑。……捕拿首要,慰我万民。尔丰诸凶,业已就擒。逆党解散……诛戮赵逆,万众欢迎。阖城居民,业已安定……天佑皇汉,鄂军倡义,宛平底定。尔丰迫于大势,仓皇去位,尚复拥兵自固,阴为鬼蜮,遂成十月十八之变,纵其部曲,肆行劫掠,公私财产,荡尽无余,满目痍疮,惨不忍睹。尔丰尚敢召集散卒,征调边兵,谋为凶逆。幸赖人心思汉,不为动摇,义师云集,壮士誓死,我军政府危而复安。尔丰仍盘踞旧署,徘徊观变,散布谣言,使民惊疑,其居心实不可问” [9]。
从新闻文告中看,赵尔丰确实是“成都兵变”的幕后黑手。但在军政府叙述兵变的通告中并未明确说明赵尔丰与兵变的关系,只是说
“乃独立之第三日,前副都督朱庆澜言称各营兵士不守纪律,不奉命令,顿反前行,不知何故?于是因疑生惧,因惧生阻,应办各事,一律停搁,每日电催数四,到军政府不过一二小时。前都督蒲提议组织陆军部不能成,提议组织参谋部不能成,提议传见军官换给札委不能成,提议行犒军礼不能成。至十六七等日,虽勉强集事,而军心已被人煽乱矣。十八日东较场简兵换札,遂起巨变,点名甫毕,既闻哄闹,不知何语。前都督蒲方传语诘问未得返答,朱已先去。旋闻枪声四起” [10]。
从新闻文告和政府文告的对比来看,显然赵尔丰是否是兵变的幕后者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刻意地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因为尹昌衡自己也说:“民军闻清祚既改,尔丰之未诛也,四方来集,郊野皆盈。曰: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未酬,奈何即罢?环城远近,凡数十万众。张培爵在重庆,谢汝翼在宁远,及李绍伊、周鸿钩皆以此收民心,谋伐成都。傅华封令于军曰:赵督犹在成都,河鱼腹疾,可克也。东犯日急” [11]。可见强化赵尔丰负面形象以增强自身合法性不仅仅是军政府的主观要求,客观形势亦使得其不得不为之。
总之,尹昌衡通过对赵尔丰负面形象的强化,不仅增强了军政府合法性,亦使得自身的合法性得到增强,并使军政府的合法性与自身的合法性逐渐合流。
3. 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
尹昌衡在动摇旧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对军政府的合法性进行建构。辛亥革命后,多种革命力量在四川并存。既有以尹昌衡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也有以张培爵为首的蜀军军政府,还有同志军(民军)、哥老会等等。如何整合这些力量成为革命后的首要问题。合法性则成为整合因素中的关键,而构建合法性的基础则是革命的正统性。正统论属于传统政治理论范畴,其中以欧阳修的正统论最具影响。依据欧阳修《正统论》的标准,正统乃“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即帝王统治天下的理由与资格。“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是衡量正统的标准 [12]。但在欧阳修的论说当中“居正”的重要性显然弱于“一统”,根本要素在于谁能够“合天下于一”,即便得位不正,亦可称之为“正统”。也就是说,谁能整合这些力量,谁就是革命的正统。因为一个政权有效性合法性指的就是政权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13]。而革命后的稳定就是最好的公共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一四川成为彰显革命正统性以及政权合法性最关键因素。
尹昌衡统一四川过程中,采取先易后难的战略即先收服同志军(民军)、其次击败傅华丰、最后川渝实现和平统一。
首先是收服民军。尹昌衡在自记中说:
“方尔丰之踞成都也,民军皆来会。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彭大均、陈和尚与焉。周鸿钧、李绍伊亦遣其将谋裂土,皆欲得官爵……乃令彭光烈料民军,日收驯而健者万人,余给资罢去。民军部辖固争之……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素明良,愿自效,则皆辟为校尉,令各统千五百人,或二千人,分巡州邑,使彭光烈统之。彭大均、李绍伊、陈和尚枭桀不受命,击斩之。刘朝望既去泸州,滇军杀周鸿钧,散其党。乃命张澜宣慰川北,邵从恩宣慰川南,颜缉祜宣慰川西,川民略定” [14]。
尹昌衡一方面安抚像吴庆熙、孙泽沛等愿意听从调遣的民军首领,另一方面剪除像彭大均、李绍伊等违抗命令的民军首领,从而将民军改编为军政府的武装力量。
其次是击败傅华丰。正是由于收服了民军,促使军政府无后顾之忧,并能够使将新改编的民军用来对抗傅华丰。尹昌衡在自记中说:
“命彭光烈、赵南森以兵五千拒华丰,曰:两师相遇必于雅,雅有三水焉,彼乘我虚,师必速,待其争渡而侧攻之,必克。师行八日,甲申,至雅,获华丰。庚寅,以华丰至,予释其缚,饮之酒,而以其军为卫” [14]。
而彭光烈所统率的正是刚收服的民军。在击败傅华丰后,尹昌衡将傅华丰的部队改编为自己的卫戍部队,从而更加增强了四川军政府的实力。这一战促使军政府威信大增,尹昌衡不无自豪地说:
“滇、渝闻之,曰:华丰兵出西康,转战四千里,两年之间未尝败北,今之如反掌,成都未可轻也” [14]。
最后是川渝实现和平统一。尹昌衡在平定民军和傅华丰后开始着手川渝的和平统一,他在给重庆军政府的电文中说:
“睽隔千里,闻与实违。中情未通,祸机隐伏。危哉!滇谍频窥,藏警日急,既不能绝萑苻以靖民,又不能竭罗掘以备用。蒿目全局,此何时耶?同力合作,犹恐不支,分党异谋,势成两败。衡心酸痛,莫可言状。以衡受任危难,兵不满三百,财不满十万,区区之心,微特忘利,固已誓不欲生矣。是以招叛合离,单骑直赴,斩逆诛乱,自分身殉,稍见一隙转机。业经数次辞职,邦人坚不我许,而扶病强支,任怨力行,何尝须臾忘大局哉?于赵则力诛之,于傅则力擒之,于滇则以百忍图两全,于渝则以一介和四督。当抚当战,尽出公仁,一行一言,悉昭大义。衡虽不才,心固同于皎日矣。而恶耗频来,谓渝中众矢,日集于衡,树党组兵,势在必举。噫!其果然欤?其果然欤?夫渝兵强不及傅、赵,而衡众已踰于曩时,武力相对,我辈必胜。然衡非犬豕,宁忍以兵乱扰桑梓哉!一兵来,衡以单骑迎。千军来,衡亦以单骑迎。两川之利是图,七尺之躯何惜?有能驭众安民,衡必推权逊位,此一贤者取之耳。树党组兵,胡为者?果其关怀大局,请即联袂而来,闻衡之言,考衡之行,鉴衡之心迹,允定公罪,而议去留,何迟之有?若夫外纵谤讥之口,内怀不测之谋,开揖盗之门,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谁洗?风雨漂摇,阋墙自哄,自非丧心,宁忍误国?岂可以全川之生命财产,供吾辈私心一赌哉?成渝不可以分立,虽妇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无不知之。衡岂忍拥权挟私,以坏大局,践约图名,以顾小信?故自愿闻命而退。至若不闻衡之言,不考衡之行,不察衡之心迹,必使于谦含冤于九原,张巡受谤于身后。衡虽有勇,不忍与渝战,衡虽有智,不忍为己谋。岳忠武无跋扈之心,檀道济有长城之叹,固所不惜。至于兵乱政纷,敌入民死,赤地焦土,败国亡家,非衡之仁所能爱护也。临书涕零,不知所云” [15]。
电文的含意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一是表明尹昌衡为四川大局不顾个人安危,在“兵不满三百,财不满十万”的艰难条件下平定成都兵变,进而擒杀赵尔丰,击败傅华封,对滇、渝则力求和平。他的言行本诸公仁和大义,是一位堪比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之士。二是强调川省面临“滇谍频窥,藏警日急”的危局,成渝双方应和平统一,而不可以分立,以张培爵为代表的渝方竟“树党组兵”反对他尹昌衡,势必危害全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是他统率的成都军队是仁义之师,且实力今非昔比,远过渝中兵力,一旦双方交战,“强不及傅、赵”的渝兵必败无疑。该函语气软硬兼施,既有关于仁义道德的表白,同时又警告渝方不要进兵成都,而应服从尹昌衡统一四川的大业 [16]。张培爵是一位识时务、比较随遇而安的革命党人。1912年1月中旬,滇、黔、湘三省通电认蜀军都督为四川都督、诋成都军政府为哥老会政府,他以四川大局为重,复电表示反对 [17]。也正因为张培爵的大局意识,促使川渝实现和平统一,为四川的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当时的南北和谈提供了参考的范本。
统一四川是彰显其革命正统性的关键因素,也是其建构军政府合法性的根基。四川军政府在尹昌衡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挑战,实现了四川的统一,对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4. 打造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一个政权维系的基础是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和行使。但几乎所有的政体,其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众的同意和认可。一个政权能够被民众同意和认可,因而被民众所自愿接受,这个政权就具有合法性 [18]。民众的这种同意与认可就是政治认同。所谓的“政治认同”主要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 [19]。也就是公民对某种政治单位、地理区域和团体的归属感。
川渝虽然和平统一,但统一之后面临多重矛盾。首先体现在双方对军政府名分之争。成都第一条是“成都为政治中枢”,重庆第一条就要求“大汉四川军政府应改名为‘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双方争取主次的意思很明显。其次是关于正副都督的职位之争。成都的第三条提出“惟须两军政府合并所成之各处、部、院职员票举选定”,名为选举,实际运行起来成都肯定占得先机。因其是中枢,重庆的张培爵到成都就任,成都选票很可能多于重庆。所以重庆军政府并未同意这条规定。最后是双方对于西征统帅人事任免上的分歧。最初任命熊克武为西征统帅是大家的共识,但因为双方因为合并事宜的种种分歧,促使熊克武不就任西征统帅,即使就任,也只在川东平匪而不去西藏,这就把难题甩给了四川军政府 [20]。
以上种种表明四川军政府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严重缺失。如何打造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成为考验政权领导人能力的试金石。当然政治认同也不是可以随意打造的,它也需要一定的时势与机缘,而四川军政府刚好兼备此二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建立了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一举成功,但新国家的建设却殊非易事。按当时广为认同、最具号召力的说法,建设五族共和的国家。按今天的说法,则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对外,国家的疆域是神圣和不可分割的;对内,国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奉行民族团结政策。但恰恰在这两方面,新国家面临着极大挑战。俄、英策动蒙、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一是危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二也说明五族中蒙、藏两族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 [20]。四川紧邻西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打造自身政治认同的天然优势。马尔克姆·安德森曾敏锐地指出,边缘地区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心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某种情况下,边疆在建立国家、塑造政治认同同时会具备一种神话意义,成为整个社会的神话构成要素” [21]。而西藏自十三世达赖返回之后,就发动了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继而,西藏地方的民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 [22]。
尹昌衡正是看到了此种机遇,所以才决定亲自西征,并将川人对自己的政治认同与对军政府的政治认同紧紧地联系起来。在6月7日四川军政府政务处专门讨论出兵西藏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亲自西征,他说:“不要再闹小事,赶紧把我们内地的精神提起,使一般人的眼光都注重到西藏一方面,把一切无味的意思、无味的竞争都放一下了,以全副精神注到那方才行。”,又说:“我们总要中国干【捍】大患御大侮岂可闹无理的事情!现在重庆与我们为难,把此话通告他们,就可以息事了。”,“不然,四川还要出无恨【限】的怪变乱来” [23]。他在《西征别川人书》中说:
“文明侈谈,则纲纪不张,横议丛生,则宵小作媒,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一也;树党朋比,顺倒是非,偏巧存心,方正裏足,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二也;纷争轧轹,互不相下,甘为散沙,以致沦胥,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三也;轻浮好变,以酿祸机,昼惊夜呼,杯弓蛇影,使人心易乱,盗生心,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四也;专法异帜,自坏长城,刚直者不肯辩诈,则悉为罪人,高明者惭与比周,则甘为废物,栋折榱崩,莫之肯护,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五也;见秋毫之末,而不睹日月,争鸡鹜之啄,而不追鸿鹄,使苍苍之士,营一枝之栖,赫赫中华,无万里之志,终致大国坐困,长材小成,是则衡深以为忧者六也。如能本诚求实,立武健严直之法,扫废弛放纵之气,冒野蜜之名,以成富强之实,则民国之精神,可超于寰宇。内不辟亲,外不辟仇,党以正合,事惟义举,则生聚之休福,可延于无穷。平心静气,惟好是从,曲己伸人,惟一是式,和国出军,和军进战,以期共济,则完美之金瓯,可固而无缺。兵成棊布,政则渐理,萑苻尽歼,军令已肃,乱极之余,美备固难臻,而反侧之间,镇静可以定,果危词不摇,民安其居,则疑似之乱机,可化于无形” [24]。
由此可以看出,尹昌衡对西征最大的期望就是“疑似之乱机,可化于无形”,也就是塑造各方势力对军政府的政治认同。
当然尹昌衡西征的决定也很快得到了四川社会各界的强烈支持。其在军界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赢得了军界空前的支持,
“自十八乱后,我接事以来,深知疑为害甚大,乃事事推诚待人,绝无半点成见存胸中。十九的一天,黄标长回来,众人都说要推倒他,不准他进来,恐他要闹事。我独往三桥上去接他……都是单人独马,办这几件事,也因如我不疑人,所以人亦自不疑我。又如西军……如若不然,你们互相猜忌,小人遂乘间而播弄之,还有不坏事的吗?大家赞成我这个话否?赞成的就请起立(众全体起立赞成)……(四)勿听谗言。昌衡此次亲征西藏,也是因为自己身为都督,看到土地丧失,本是很可耻的。故这样的重大的担子,敢一力担起。但是,这内里头的事,如果不布置完善,心里常常就不免有内顾忧……大众如无他意,就请起立(众全体起立,拍掌赞成)” [25]。
而西征军的誓师大会更是赢得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上海《民立报》记录了当时现场的情况:
七月十日,尹都督率西征军大本营出发,各学校各法团及军政界中人送于武侯祠者,不下数万,诚盛举也。尤可羡者,模范两等学校学生,其幼者不过五六龄,服军服,唱军歌,步法亦整整齐齐,见者莫不惊羡。弱质之女学界亦不避酷暑,行于烈日中,以表欢送之意……末由张都督举手呼西征军万岁者三,万众拍掌之声如雷震,遂行” [26]。
作为职业军人和民国地方官员,尹昌衡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可否认,但在川省政局乱象纷呈的情况下,作为省督的尹昌衡主动提出远征以赢得政治认同也无可厚非。对处于权力、利益角力中的政治家而言,最恰当的取向就是把斗争掌握在可控范围,不致酿成大事端,破坏国家大局。如果用这个标准评价尹昌衡西征,他做得恰到好处。
5. 结语
尹昌衡通过强化赵尔丰的负面形象、彰显其革命的正统性以及打造新政府的政治认同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地塑造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国家的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军政府的合法性与尹昌衡的个人权威也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军政府的合法性与尹昌衡个人的权威逐渐合流,并最终成为了一体。随着尹昌衡的北上被禁,军政府的合法性亦随之瓦解,亦为后来四川的长期分裂埋下了祸根,这也是尹昌衡当日所未料及到的。
文章引用
王 宝. 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合法性的塑造
The Shaping of Yin Changheng and Sichuan Military Government's Legitimac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04): 496-50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70
参考文献
- 1. 张星久.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482-489.
- 2.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性危机[J].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7.
- 3.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五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978.
- 4. 王炎. 尹昌衡和他的时代[J]. 中华文化论坛, 2012(2): 87-88.
- 5. 龚克. 从赵尔丰到“赵屠夫”[J]. 四川档案, 2014(6): 43-44.
- 6.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2.
- 7.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三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894.
- 8.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7.
- 9.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8-19.
- 10.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3.
- 11.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三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01.
- 12. 张春林.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186-192.
- 13.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与国家社会关系[J]. 学术月刊, 2016(8): 167-178.
- 14.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三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04.
- 15.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三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05.
- 16. 周斌. “与张培爵书”辨析[J]. 近代史研究, 2012(6): 143-144.
- 17. 周开庆. 民国川事纪要[M]. 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23.
- 18. 让-马克•夸克. 合法性与政治[M]. 佟心平, 王远飞,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2-35.
- 19. 罗森邦. 政治文化[M]. 陈鸿瑜, 译.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4: 69.
- 20. 吴燕, 刘一民. 尹昌衡西征三题[J]. 近代史研究, 2013(3): 95-109.
- 21. 刘晓原. 边缘地带的革命[M]. 万芷均, 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 9-10.
- 22. 任新建, 何洁. 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9.
- 23. 吴燕, 刘一民. 尹昌衡西征三题[J]. 近代史研究, 2013(3): 102.
- 24.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72.
- 25.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76-177.
- 26. 曾业英, 周斌. 尹昌衡集[M]. 第一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78-179.
NOTES
1主要有:邱远应《赵尔丰发动“成都兵变”说质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5期),冯静、万华《再评辛亥革命中的赵尔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5期),李茂郁《论赵尔丰》(《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顾旭娥《赵尔丰与清末川边新政》(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 年),陈枫《论赵尔丰与“成都兵变”》(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 年),鲜于浩《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