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Vol.
07
No.
03
(
2019
), Article ID:
31344
,
10
pages
10.12677/OJLS.2019.73009
Criminal Law Study on “Clash of Bus Drivers and Passengers”
Yubo Yao
Law School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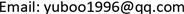
Received: Jul. 1st, 2019; accepted: Jul. 15th, 2019; published: Jul. 22nd, 2019

ABSTRACT
In the criminal cases caused by “striving conflicts”, there are problems of excessive evaluation and fuzzy evalu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case is rather rough. The existing offences cannot cover passengers’ nuisances of safe driv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d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to accurately evaluate such behaviors. The purpose of the regulation is to compensate for the public risks that do not have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arson explosion. The situation, the actual infringement of public safety or the qualitative gap in the specific dangerous situ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rime is briefly designed. For the driver’s behavior of “professional driving position”, the type analysi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current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able to complete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viewpoint of conviction should also be ne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harm, criminal law and modes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Keywords:Conflicts between Drivers and Passengers, Driving Crimes of Safe Driving, Dangerous Methods of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Specific Dangerous Criminals
公交车“司乘冲突”的刑法透视
姚宇波
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 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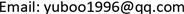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9年7月1日;录用日期:2019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19年7月22日

摘 要
对于“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过高评价、模糊评价的问题,案件的定性较为粗糙。现有的罪名无法涵盖乘客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有必要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准确评价此类行为,其规范目的在于弥补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造成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同质性的公共危险的情形,对发生公共安全的实际侵害或具体危险场合下的定性空白,在此基础上对该罪的构成进行简要的设计。而对于司机“擅离驾驶岗位”的行为则应进行类型化的分析,现行治理体系已经能够完成准确解释和评价,从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以及程序的效率与公正等角度也应否定入罪的观点。
关键词 :司乘冲突,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危险犯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8年10月28日,重庆市万州区发生公交车坠江事件,对于该事件的刑法性质与防范对策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与探讨。司法实践中,对于司乘冲突所引发刑事案件的处理较为粗糙,存在“同案异判”现象,因此理论上有必要梳理现有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构建出更为精细而审慎的定性路径。
2. 公交车上“司乘冲突”的刑事司法现状评析
从以往刑事判决结果看,对于乘客与司机因争执互殴引发重大事故,该如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一) “司乘冲突”刑事案件的类型分析
1、乘客行为引发“司乘互殴”致车辆失去控制
该类“司乘冲突”案件以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为典型 [1] 。此类案件中,乘客行为引发驾驶人员擅离职守,其以行为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为主要特征。乘客行为多表现为双方口角或者程序较轻的攻击行为,其行为不足以致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从因果关系看,乘客、司机的行为均与结果的发生有关,均存在形式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但刑法中因果关系须进一步考察实质上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从规范或价值的角度分析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2、乘客行为直接导致车辆失控
在此类案件中,乘客行为通常表现为在车辆行使过程中,采取身体攻击、暴力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等使得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车辆失控引发交通事故与乘客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乘客主观方面的不同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在祝久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乘客祝某殴打司机、争夺变速杆,导致公交车失控,造成直接损失近万元,法院判决祝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孙某某寻衅滋事案中,乘客孙某某殴打司机王某,同时拔掉公交车启动钥匙,又将王某某拉出驾驶室,自行坐进驾驶座开启公交车电源,乱按操作台上的按钮,在与王某的争执中,用弹簧刀将王某划伤,法院判决乘客寻衅滋事罪。
(二) “司乘冲突”刑事案件的定性分析
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过度评价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危险方法”有特定要求,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2] 将乘客采取身体攻击、暴力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等使得驾驶人员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的行为,一概认定为该罪过于粗糙,容易导致错误定性。笔者认为,对于乘客的行为应结合客观因素,如公交车行驶的路段、车速、车内乘客及车外路人、车辆等,具体判断该行为是否引发了同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公共危险,如公交车行驶在乡村路段,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因司机及时刹车而未导致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应当说从当时的情况未产生现实而紧迫的高度公共危险,将此一行为评价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适当的。那么如何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笔者认为,由于此种情形下,抢夺方向盘的行为所造成的危险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引发的危险具有同质性,难以对行为人科以刑责,只能对其行政处罚。
同样,对于司机的行为评价也应关注其他客观因素,若城乡公交的司机在人烟稀少的乡村路段行驶,恰好车内的仅有个别乘客,此时司机与乘客发生冲突,类型一中司机擅离岗位的行为难以认定为公共安全的犯罪,“公共”安全必须体现一定程度的不特定性或者多数性、公众性、社会性,此种情形下侵害的对象不具有向多数拓展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成立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如故意伤害罪。
2、交通肇事罪难以准确评价乘客行为
对类型一中的乘客定性为交通肇事罪值得商榷。以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为例。从客观要件看,危害结果虽然达到司法解释的要求,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万左右的财产损失,但由乘客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并不妥,责任的认定须依赖于行为、结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乘客斗殴与司机离开驾驶岗位具有条件关系,即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但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满足于形式关系的判断,更应对实质关系进行判断,刑法理论存在诸如“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危险的现实化说”的不同理解,从笔者支持的“危险的现实化说”来看,行为须具有内在的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结果的发生是实行行为所包含的危险的现实化。首先,乘客仅挥拳击打了司机脸部,司机完全能继续保持安全驾驶,该殴打行为引起结果的危险性低,其次司机离开驾驶室这一介入因素并不是经常伴随乘客殴打这一实行行为而发生,公交司机具有特殊性,应当说合格而理智的司机在这种情形下不会选择在车辆行进的过程中,置车上乘客利益不顾而贸然起身进行互殴。司机的行为应是独立地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即使是从作为通说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折中说理解,作为一般人的乘客对于公交司机的基本素质具有合理的期待,即认为公交司机在被拳击打后不会贸然起身与自己互殴,至少也应当是将车挺稳后才离开驾驶室,因此公交司机的行为已经能超出一般人的认知,其发生属于罕见的情形,乘客的殴打行为与交通事故并不具有因果关系,难以将其归责于乘客。总之,就本案而言,该乘客宜做无罪处理,对其行政处罚即可完成责任追究。
在实践中,对于乘客的抢夺变速杆、方向盘等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常出现争议。焦点在于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根据“罪疑唯轻”的原则,当出现模棱两可时应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与判断,实践中却往往与原则相背离,即当被告人罪过形态出现疑问时,法院更倾向于认定为故意犯罪。因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的现象,学者认为体现了大众舆论对于“重刑主义”的追求 [3] 。从规范的角度看,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其一是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其二是对该公共危险的主观心理态度。学界对于危险程度有诸多探讨,可以从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概率、结果影响的范围等方面来判断,对于主观心理态度的区分,站在动机说的立场,过失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应当并且也能够认识犯罪事实,由于不注意却没有认识,以致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但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公共危险,且对具体的公共危险没有认识和预见,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实施了具有高度危险的驾驶行为,在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况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对危害结果没有认识或预见的情况则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诸多由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中,乘客抢夺变速杆是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作为一般人应认识到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不能被干扰,变速杆作为驾驶汽车的关键装置,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危及公共安全,行为人认识到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刑法规范期待行为人“形成反对动机”,但行为人辜负了刑法的期待,因此乘客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类的故意犯罪。但究竟定何罪,实践一般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学者认为应避免该罪“口袋化”,此种行为的实质是妨碍交通工具正常功能的发挥,足以使汽车发生颠覆、毁坏危险,与劫持火车的行为具有共同本质 [4] ,宜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 [5] 。
本文认为,从刑法条文看,两罪的刑罚幅度具有一致性,侵害的法益也均是公共安全,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优先适用特别法,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但是适用的前提是符合该罪的构成,客观上的破坏需要使得交通工具本身遭受整体损坏或失去原有功能足以使车辆倾倒,具体到司乘冲突案中,若乘客抢夺方向盘、变速杆不足以使得车辆倾倒,如使得公交车路线失控,冲进人群,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乘客对方向盘、变速杆等实施了破坏行为导致车辆失控,则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
3、寻衅滋事罪的评价不足
由于该罪在司法适用中欠缺可操作性,构成要件上的非独特性,学者称之为“口袋罪” [6] ,在理论上面临存废之争。乘客在公交车上殴打司机符合该罪“随意殴打他人”这一表现形式,司乘冲突多因“下车”、车费而起,可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随意性。司法大数据显示,有14.74%的乘客被定为寻衅滋事罪。
然而将乘客抢夺方向盘或与司机斗殴等行为定为寻衅滋事罪却是一种无奈之举,此种评价无法涵盖乘客行为的刑法属性。应当认识到去罪化是寻衅滋事罪的最终路向,在司法适用中先进行软化和弱化的处理,在不得不动用刑罚时也应优先选择其他罪名,保持适用中的克制。更为重要的是,诸如乘客抢夺方向盘等行为除了侵害社会管理秩序外也侵害了公共安全,而寻衅滋事罪无法涵盖公共安全这一法益,这一法律评价未体现此类案件发生的特定情形——公共交通工具上,寻衅滋事罪实属在现行刑法中缺少能准确评价行为的罪名的无奈之举。
3. 乘客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万州公交车坠江案发生后,胡云腾大法官主张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抢夺方向盘威胁公共安全”入罪,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同时参考危险驾驶罪的量刑。
(一)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规范目的
实践中对于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的处理存在过度评价与模糊评价的问题。具言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某些情形下会造成过度评价,同类解释规则要求危害行为所引发的危险具有与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危险,此外,强调危险方法的“一次性”,意味着一旦行为实施便无法立即控制结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意味着行为必须具有“具体危险性”,仅造成抽象危险的不能构成该罪。而实践中对于以上诸多入罪的限制条件多有突破,在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中,乘客抢夺方向盘、变速杆或殴打司机,在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行为当时至多具有一般具体公共危险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是一种过度评价,例如公交车行驶在车、行人稀少的乡村路段,车内仅有个别乘客情况下,乘客殴打司机,由于司机刹车及时未造成危害后果,此种情形评价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合适的;交通肇事罪的适用面狭窄,该罪要求客观上必须发生一定程度的实害结果,且乘客主观上对实害结果是过失,因此对于乘客行为造成具体公共危险或对实害结果有预见的场合无法构成交通肇事罪,现实中发生的大量司乘冲突并未造成实害结果,且作为一般人在行为当时对危险结果是有认识和预见的;寻衅滋事罪的模糊评价、评价不足,其本身作为“口袋罪”就受到学者的质疑,运用该罪无可避免得存在模糊性,更重要的是该罪侵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司乘冲突中,乘客的行为多是侵害了公共安全,仅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忽略了“危害公共安全”一面,未对危害行为作出完整评价。在现有的罪名无法涵盖乘客行为的情况下,有必要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以准确评价行为。
乘客殴打、拉拽公交车司机,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的行为,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破坏交通工具罪、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等。具体包括以下情形:
1、乘客的行为产生了与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高度危险,例如公交车行驶在窄桥、车辆多的高速公路、人员极为密集区或者乘客的严重暴力行为、抢夺方向盘变速杆导致公交车驾驶员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乘客的行为在实施之后,其可能造成的危险或实害结果无法立即得到控制,可以认为乘客的行为属于刑法114、115条中的“危险方法”。在造成实害结果的场合,若乘客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认识和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同时对实害结果是过失,可能同时触犯交通肇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过失结果加重犯,与此相对,对实害结果若是故意,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结果加重犯。若乘客对具体的公共危险以及实害结果主观上是过失,则可能同时触犯交通肇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未造成实害的场合,若乘客主观上对于具体的公共危险有认识和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主观上对此具体的公共危险存在过失,则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乘客的行为造成了公共危险,但是其“危险”与放火、爆炸等不具有同质性,如乘客的殴打行为、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行为不足以使得司机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公交车司机仍然能够对乘客行为引起的危险作出及时反应,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结果。在造成实害后果的场合,张明楷教授认为劫持火车电车宜认定为破坏交通工具罪,有学者基于此进一步认为乘客的殴打拉扯行为可以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理由在于该行为在性质上可以等同于劫持火车电车的行为,同样是妨碍了车辆功能的正常发挥。但本文认为,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客观上仍然要求行为使得车辆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如果将所有乘客的行为都一律评价为破坏交通工具罪,似乎过于扩大了破坏交通工具罪,有类推解释的嫌疑,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使车辆倾覆毁坏继而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乘客殴打、拉拽,抢方向盘等行为难以说其具有使车辆倾覆、毁坏的故意。因此,在发生实害结果的场合,若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现行刑法并没有合适的罪名予以评价,若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则可构成交通肇事罪。在发生具体危险的场合,现行刑法也无法作出准确的评价,仅作为一般违法处理。
因此,为准确评价乘客的行为,主张增设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其规范目的应当在于,弥补现行刑法对于乘客故意实施殴打、拉扯司机、抢夺方向盘等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造成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等同质性的公共危险的情形,对发生公共安全的实际侵害或具体危险场合下的空白。
(二) 妨害安全驾罪构成的理论设计
妨害安全驾驶罪应当属于具体危险犯,并有结果加重犯情形。对于具体危险犯的量刑可以参照危险驾驶罪,对于结果加重犯的量刑幅度可以参考刑法119条破坏交通工具罪。
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抢夺方向盘威胁公共安全”等使得公交车司机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减弱的行为,危害结果为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造成危害或现实侵害结果。
主观上,行为人故意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对于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预见或认识,并放任或追求这种危险结果发生;行为人未预见具体的公共危险,主观上是过失的情形可以构成过失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竞合。
4. 司机擅离驾驶岗位的行为——建议慎重动用刑法手段
在重庆万州沸沸扬扬的公交车坠江案发生后,司乘冲突所引发的刑事案件成为法律学人关注的焦点。最高院大法官胡云腾建议,可在现有的危险驾驶罪四种情形外增加一条,即“以其他方法“,可以包括司机长时间玩手机、与乘客发生纠纷后离开驾驶室去打架、骂架等情形。这些行为是否有必要入罪以及入罪后与现行的治理格局能否适应,笔者基本观点为,将公交车司机擅离驾驶岗位行为入罪既无必要,又与现行的治理体系不适应。
(一) 司机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本文认为,公交车司机擅离驾驶岗位的行为在客观上大体可划分为“完全脱离驾驶状态”以及“未完全脱离驾驶状态”两种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的不同,成立不同的犯罪。
1、完全脱离驾驶状态的情形
此种情形特点在于一旦发生危害后果,无法立即得到控制,如公交车司机离开驾驶室、“忘乎所以”地玩手机等,因此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引起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性,与放火、爆炸、决水等造成的危险具有同质性。主观上,作为一个经过专业培训和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公交车司机应当认识到在驾驶过程中离开驾驶岗位,完全脱离驾驶状态,会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有可能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行为人对于具体公共危险具有认识,但是行为人对于实害结果则可能存在故意与过失。可能涉及的罪名有破坏交通工具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交通肇事罪。具体而言。
车辆失控造成了不特定或多数人生命或重大财产侵害的情形。若行为人主观上对此实害结果具有过失,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可适用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结果加重犯)的想象竞合;若行为人主观上对实害结果具有故意,即明知可能发生公共安全被实际侵害的后果,此种情形,也适用刑法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公交车司机实施“完全脱离驾驶状态”的行为未导致实害结果发生。在造成具体危险的情形,由于主观上对于与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具体的公共危险有认识,此时应适用刑法第114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仅造成抽象危险的情形,如司机离开驾驶室与乘客斗殴,由于其他乘客的阻止,使司机及时回到驾驶岗位,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发生。从一般经验来看,行为人的行为使得车辆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应当认可其属于可罚的危险,但何种罪名如何做出正确的评价呢?本文认为,若作为“其他情形”纳入危险驾驶罪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该行为的危险程度明显大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四种情形,以“醉驾”为例,其可罚性也仅仅在于行为人处于醉酒状态,反应能力减弱,行为人一定意义上仍处于驾驶状态并非完全脱离,因此危险驾驶罪不足以评价“完全脱离驾驶状态”,对此,本文认为可成立刑法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但并非所有造成抽象危险的场合都作为犯罪处理,若驾驶员只是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处于“完全脱离状态”,例如,在驾驶的过程中伸了一个懒腰、双手脱离方向盘看了一下手机(脚也离开刹车、油门等),此种情形由于车辆实际上仍然处于司机控制之内,在没有造成法益侵害或威胁的场合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而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此时若因司机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实际发生,应认为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交通肇事罪。
公交车司机卷入与乘客的斗殴行为(并非还手)。斗殴不同于还手,客观上斗殴一般表现为双方之间重复的攻击行为,司机已经脱离驾驶状态,而还手仅仅表现为一方的还击行为,不具有重复性,司机仍然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车辆,主观上斗殴具有明显的故意,而还手则可表现为过失。由于斗殴行为的特点,其任何一方都无法立即控制结果,也就是说司机不可能迅速脱离殴打状态,此时司机的行为与一旦实施就无法立即控制结果的爆炸、决水等具有同质性,因此,不论司机是用一只手打还是一条腿踢,只要多次主动攻击乘客与其相互扭打在一起,均应认为客观上处于“完全脱离驾驶状态”。
2、未完全脱离驾驶状态的情形
此种情形的特点在于车辆尚处于公交车司机手或脚的控制之中,如公交车司机在驾驶过程中长时间玩手机、在被乘客殴打后还手,若手仍在控制方向盘,如司机脚踢乘客以还击,此时的后果是不能及时刹车;若脚仍在控制车辆,如司机在玩手机,此时的后果是不能及时控制方向。因此,此种情形下是由于司机的行为导致对于驾驶的反应能力减弱,无法对紧急情况作出应对,导致事故发生,危及公共安全利益。“未完全脱离驾驶”状态所实施的行为虽然也能引起公共安全利益被侵害,但是由于只是反应能力减弱,即使行为发生,司机若反应及时,也能够立即控制结果发生,因此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同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高度危险,在例外的情形中,若公交车行驶在窄桥、车辆多的高速公路、人员极为密集区等,也可以认为其“危险”达到了与放火爆炸等具有同质性的高度危险,理由在于在高度危险的路段驾驶,一旦行为发生,即使司机反应及时,也难以避免结果发生。主观上,行为人可能认识、预见到具体的公共危险发生,也可能没有认识或预见,在发生实害结果的场合,行为人对于实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
在具有高度危险的道路上行驶,由于其危险达到了与放火、爆炸同质的高度危险,因此,本文认为可以放在“完全脱离驾驶状态”中作相同的评价。需要补充的是,行为人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可能没有认识,如公交车在一个往常人流稀少的路段行驶,行为当时由于特殊情况聚集了大量人群,公交车司机玩手机时由于并未意识到行驶在该路段会发生突发情况,即未意识到客观上的具体的公共危险,在发生了实际侵害公共安全的场合,若行为人主观上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一般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种情况下,若未造成实害结果,由于行为人并未认识到具体的危险,不能依据刑法114条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应作为犯罪处理,仅为一般行政违法。
在不具有高度危险的道路上行驶,若公交车司机的行为使其处于“未完全脱离驾驶状态”,只要发生了实害结果,无论行为人对公共危险有无认识,只要对实害结果主观上是过失的,均可构成交通肇事罪,如公交车司机认为自己驾驶技术了得,即使玩手机或被乘客殴打后还击也能保持安全驾驶、公交车司机被乘客殴打后,驾驶能力出现障碍后继续开车导致事故发生等。此种情形下,若行为人对实害结果主观上是故意,此时行为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例如公交车司机被乘客殴打后怒气冲天,在道路上加速行驶,横冲直撞,若造成了车内或车外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损失,可能分别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此种情形,即使未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仅造成了具体的危险,也可以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等。
在不具有高度危险的道路上行驶,若“未完全脱离驾驶状态”的行为未造成公共安全实际损害,在造成具体公共危险的场合,若行为人对具体的危险有认识而故意实施,例如,公交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与乘客发生冲突,司机置道路两旁的行人安危不顾而还手的行为导致车辆路线偏移,若司机及时作出反应就不会造成具体的公共危险,但司机未及时采取措施,由于行人躲避及时未造成公共危险的损害后果,此种情形由于危险不具备放火爆炸等同质性的高度危险而无法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仅有在对生命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时,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外不作为犯罪处理,因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均是实害犯;在行为仅造成抽象危险的场合,也不应当作为犯罪,理由在于,并未对法益造成侵害或威胁,若作为犯罪处理,显然是与前述“造成具体危险情形”的后果不协调。具体而言,“造成具体危险的场合”也仅在现实紧迫地威胁到生命了才构成犯罪,而一旦将“抽象危险场合”入罪,意味着引起低程度的危险均是犯罪,而引起高程度的危险很大可能不是犯罪。
通过对司机“擅离岗位行为”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并不存在“司机擅离驾驶岗位”适用危险驾驶罪的空间,现行刑法已经能对该类行为作出合适的解释与法律评价,入罪则会导致现有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的矛盾。
(二) 社会危害性:结果无价值的立场
探讨一个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应关注行为的性质,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判断,入罪的最低限度就是行为必须产生抽象的危险,若抽象的危险也不具备则不可能作为犯罪处理。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具有社会危害性未必是犯罪,包括犯罪在内的任何违法行为都是对社会无益的危害行为,一般违法与犯罪的本质区别在于“量”即危害社会程度的高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7] 。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存在不同观点。结果无价值论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础,认为“无法益侵害即无犯罪”,在判断社会危害性时首先考虑危害结果,成立犯罪必须要造成侵害或威胁法益的结果,且在判断过程中不能混入行为人主观因素;而行为无价值论以“规范违反说”为基础,二元论者认为刑法上的实质社会危害性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或危险,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中不仅要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法益,还应考虑其是否偏离社会相当性的要求。社会相当性的概念实际上被具体化为“社会一般观念”,社会人一般看法、或者说是“公众认同” [8] ,如学者在论证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 [9] ,而这在本文所采的结果无价值看来是不可取的。在风险刑法观和一般预防论的影响下,德日刑法普遍体现出刑事立法普遍化与刑事处罚提前化,抽象危险犯的出现就是其体现。结果无价值以结果为本位,认为只要侵害法益,原则上就成立犯罪,抽象危险亦不例外,只是其侵害法益的危险仅达到了抽象程度,是将“危险”作为立法理由,而没有像具体危险犯那样将“危险”作为犯罪成立条件 [10] 。危险的判断要求一般人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运用经验法则判断,若此种情况一般会发生后续侵害法益结果则能被作为犯罪处理。放到公交车司机擅离驾驶岗位行为中来看,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短暂地离开驾驶状态,车辆仍在司机的掌控之中,即使发生路线偏离也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调整,并未对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安全法益造成危险。此外,从生活经验来看,公交车司机往往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与超出一般的驾驶技能,加之公交公司对于司机的严格管理规范,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更加注意安全和规范,现实中公交车司机玩手机、与乘客互相斗殴的也极其少见,即使看手机或者还手也可以凭借其驾驶技能、反应能力,可以保持在安全驾驶的限度之内。因此,站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从社会危害性考量,单纯的在驾驶过程中玩手机、被打后还手不足以作为犯罪处理,至多是一般违法行为。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主流刑法思潮已经逐步摆脱了对犯罪进行实质评价的理论窠臼,转而从犯罪的形式定义出发研讨犯罪的含义,因此以‘社会危害性’的存在与否作为‘毒驾入刑’的正当化理由,至少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 [11] 。这实际是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应入罪无须考察社会危害性,而只需关注行为本身。无论是结果无价值论还是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都无法认可,即使是在风险刑法之下,犯罪是侵害或威胁法益的根本观点也不应动摇。
(三) 刑法谦抑原则: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非协调性
刑法以谦抑性作为其立法的理性,入罪时应保持克制,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发生,刑法不应急于介入。这种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应当被尤其强调。理由在于,我国对于违法行为是一种不同于德日的二元化的结构,构成犯罪需要达到刑法所规定的质和量,若未达量的要求,则可能转而受《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而德日在犯罪构成中缺少定量因素,偷一分钱可能就是盗窃罪。
针对公交车司机的行为,需要考察现有的行政处罚是否能有效遏制此种行为?这一方面目前缺少实证的研究,只能从规范的角度分析。《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款规定,驾驶员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通过查阅多个省的实施办法,对于此类司机行为,均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理,罚款最高为200元,最低为50元。行政法规应从便捷管理的角度作出适时的调整,可是对于此类行为,处罚极为轻微,可见,在行政管理者看来,这样的处罚已经足以应对该类违法行为,不存在刑法干预的空间。对于这样一种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一跃成为犯罪显然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可能有人认为,公交车司机具有特殊性,应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驾驶普通机动车玩手机属于违法行为而驾驶公交车玩手机则构成犯罪。然而这看似合理的说法实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两者危害社会的程度无法比较,如在公交车内没有乘客或仅有少量乘客的情况,此时公交车与一般机动车无异,公交车司机玩手机与一般机动车司机玩手机的危害社会的程度相当,没有理由将其中一种行为定为违法行为将另一种行为认定犯罪。其次,仅将公交车司机玩手机行为入罪,从而否认一般机动车司机玩手机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不恰当的。若危险驾驶罪扩张至公交车司机玩手机意味着将该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纳入刑法的视野。通过法律拟制认定该行为属于足以侵害法益的行为,具体而言,刑法认为公交车司机玩手机足以引起公共安全利益被侵害,但是,一般机动车司机玩手机同样也足以引起公共安全利益被侵害,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公共利益表现为车内与车外,后者仅包括车外,但是这样的差别能够说明前者的公共利益更加值得保护吗?笔者认为无法简单衡量,如大型货车司机与公交车司机在相同的路段玩手机,显然,货车司机相较公交司机行为更加足以引起法益被侵害。立法不能将一种程度更轻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将程度更重的行为简单认定为一般违法,否则就会造成行为与责任的严重不适应。
(四) 程序法上的效率与公正
刑法手段注重公正,行政手段偏重效率。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的重要区别在于程序的不同,程序所注重的价值也是各有侧重。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围绕被告人的权益而展开,刑事诉讼旨在于通过程序的设置,使得国家刑罚权在保障被告人正当权利的基础上得以正确实现。程序法的价值并仅在于保障实体法正确落实这样的工具意义上,更重要的是程序具有的内在价值,程序自身能够蕴含公正、平等、效率等独立价值,这就是刑事诉讼程序不应成为“治罪程序”的价值缘由,如果是刑事诉讼的全部或主要的意义在于落实惩罚犯罪,那么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本身就是对这一意义的最大阻碍,其恰恰是为了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肆意定罪。而行政制裁则不同,行政制裁的出发点在于实现国家管理的需要,如何实现最便捷、最有效率的管理应当是行政制裁的价值源头。
刑事制裁是一种“昂贵的正义”。刑事诉讼程序重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因此有人说整个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被告人人权不断被重视的历史。基于此,在诉讼中赋予了被告人诸多诉讼权利,如充分的辩护权,整个诉讼运行需要严格遵循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事实的认定需要充足的证据,并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诉讼行为一旦违反程序法就会面临被宣告无效的危险,因此,真是这些“定罪的障碍”使得刑事诉讼程序冗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如果以刑事诉讼程序处理轻微的反社会行为,正如学者所说的犹如“大炮轰蚊子” [12] ,得不偿失。而行政程序则以效率为导向,行政权利的直接性、主动性和广泛性使然,即使是有法律保留原则、处罚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等,也难以遏制行政权力具有的天然扩张性,原因在于行政处理程序简便易行,迅速惩罚实现管理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中,不能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为导向,刑法中的特殊预防应较一般预防更为强调,在此意义上刑法的设置目的应当是针对过去,而非面向未来。由于刑事制裁“孔武有力”,因此舆论中常出现对于一类反社会行为,动辄呼吁入罪,而未进行理性的考量,实际上,社会中出现这样的反社会行为常常是由于行政管理的缺位造成,如果能够通过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就能解决问题,就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本文所讨论的司机擅离驾驶岗位、玩手机这样的行为通过前文的类型化分析表明,显然是一种轻微的危害社会行为,刑法已经能够对类似的行为作出合理评价,就不需增设新的犯罪。
文章引用
姚宇波. 公交车“司乘冲突”的刑法透视
Criminal Law Study on “Clash of Bus Drivers and Pas-sengers”[J]. 法学, 2019, 07(03): 65-74.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19.73009
参考文献
-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 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总第28辑)[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 2. 陆诗忠.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5(5): 60-70.
- 3. 徐光华. 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J]. 法学家, 2014, 1(5): 109-124.
- 4. 张明楷. 刑法学(第五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 5. 陈洪兵.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口袋化”的实践纠偏[J]. 刑事法评论, 2015(2): 394-415.
- 6. 张训. 寻衅滋事罪该向何处去[J]. 刑事法判解, 2013(2): 180-192.
- 7. 黎宏. 刑法学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 8. 黎宏. 刑法总论的问题思考[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9. 叶良芳.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J]. 法学, 2011(2): 13.
- 10. 黎宏. 论抽象危险犯危险判断的经验法则之构建与适用[J]. 政治与法律, 2013(8): 2-9.
- 11. 包涵. 论“毒驾入刑”的正当性诉求——兼议“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和取舍[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0(5): 143-149.
- 12. 王政勋. 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J]. 法学论坛, 2011, 26(3): 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