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
08
No.
03
(
2020
), Article ID:
37864
,
8
pages
10.12677/WLS.2020.83018
论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重塑
李亚萍,闫月宁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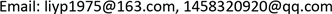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8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11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18日

摘要
李碧华的小说《青蛇》是对《白蛇传》的故事新编,相对于传说中的青蛇作为配角形象塑造较为单薄扁平的特点,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塑造颇有颠覆性意义。青蛇成为了叙述者和主角,颠覆了传统叙事文本中的忠诚不二的、扁平的丫头形象,被塑造成反叛、情欲化、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实现了“配角主角化”的翻盘。李碧华重塑青蛇形象,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传统角色的女性主义观照,从女性视角凸显青蛇的女性主体意识,彰显当代女性价值观。
关键词
李碧华,青蛇形象,重塑,反叛性
Study on Li Bihua’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Green Snake
Yaping Li, Yuening Ya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 28th, 2020; accepted: Sep. 11th, 2020; published: Sep. 18th, 2020

ABSTRACT
Li Bihua’s novel “The Green Snake” is a new compilation of the story of “White Snake Biography”. Compared with the legendary green snake as a supporting character, it is relatively thin and flat. Li Bihua’s cre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green snake is quite subversive. The green snake became the narrator and the protagonist, subverting the loyal, flat girl image in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xt, and being portrayed as a female image of rebellion, eroticism,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realizing the reversal of “supporting protagonist”. Li Bihua’s reinven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green snake very clearly expressed the author’s feminist view of this traditional role, highlighting the femal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green snake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and embodying the values of contemporary women.
Keywords:Li Bihua, Green Snake Image, Remodeling, Rebellion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文献综述
李碧华的《青蛇》完成于1986年的香港,是对《白蛇传》的故事新编。小说以青蛇为叙述者,用俏皮和无厘头的口吻讲述了青蛇在经历了世间爱情和背叛过后的人生体悟。青蛇误食七情六欲丸而情窦初开,因嫉妒白蛇与许仙相爱做了第三者,但却在最后发现了男性的自私贪婪以及爱情的虚幻,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所反思。青蛇的反叛性心理更多代表了现代女性意识,相对以往的青蛇形象更饱满,也是对传统青蛇形象的重塑。
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重塑是对传统男性创作的反叛,此时青蛇进入了女性话语体系中,颠覆了男性视角下的过于伦理化的蛇妖形象。本文力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青蛇》与其他历史文本的对读比较,挖掘作者李碧华如何完成对青蛇的重塑。本课题对感受李碧华的女性主义创作观,重新审视和认知青蛇形象,体会其中的审美价值,突出小说的文学创新意义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李碧华青蛇形象的研究分为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和青蛇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流变两个维度。大部分学者对李碧华《青蛇》的研究则多从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从青蛇对传统男性霸权的反叛展开分析。例如张衡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对李碧华《青蛇》中女性形象的重塑做了研究,认为李碧华发掘了被掩盖的小青形象和被理想化的白素贞形象,灌注了现代都市女性意识,试图打破男权中心文化中的“想象女性”的女性异化形象,在解构中重塑了女性形象 [1];韩旭东以青蛇为研究对象,以女性主义批评为方法论,挖掘作者在青蛇身上赋予的女性主义色彩,并探寻该种书写策略的成因,通过这部作品来反观香港女性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2];严虹从颠覆与重构的角度评论了《青蛇》对现代女性心理情感的书写,认为它是以一个现代女性主义者的角度讲述一个爱情故事,颠覆了传统故事的主旨,重构了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文本,深刻探讨了现代女性心理 [3]。
另一类研究则对青蛇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流变进行了简单梳理,例如候春慧则是从白蛇故事在小说、戏剧、影视等方面整体重编的过程,对李碧华《青蛇》的故事新编及叙事策略展开研究,管窥这一传说在人物重塑、文化意义和价值判断上是如何完成现代流变的 [4];张万丽则突出描写了青蛇的情欲,追寻和探究古代青蛇形象的延续和转变,其次,在包括影像资料和文本资料的分析中,对当代的青蛇形象进行梳理和阐释 [5];白杨和杜未未从《白蛇传》定型与改写中的青蛇原型擅变展开研究,剖析了《青蛇》等“故事新编”中的青蛇形象 [6]。
还有一类是从女性主义与社会政治学观点结合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例如聂焱从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家国意识结合的角度做了研究,以《青蛇》等三部小说为重点,解读女性意识和女性形象,同时试图探索女性所象征的“九七”前后的香港的命运及香港人自认为边缘人怀旧又无奈的复杂心态 [7]。
1.2. 研究框架和思路
在此研究基础上,受张衡从女孩、女人、女神的角度剖析青蛇和白蛇形象的启发,笔者认为青蛇形象可以从“蛇”的本体开始讨论,除了从女孩到女人的性格进展,还能继续补充青蛇的兽性和动物性的一面来更多面地看待其成长历程,从兽性、人性、妖性的结合进行探讨;作为主角的青蛇由蛇——人——女人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完整地展现其复杂的性格特点。与此同时,受高艳芳和焦丽君学者的启发,本文也采用历史性视角,在青蛇演变史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 [8] [9],研究不同文本下青蛇形象的流变,如此可以从横向的个体性格上和纵向的时间变化上整体剖析青蛇形象的重塑。最后本文将探讨青蛇成为叛逆女性后被作者赋予激进的女权意识,例如正视情欲是女性的正当需求、以同性恋对抗异性婚恋两个方面,并总结青蛇形象重塑的意义。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进行了大量文献搜集,对国内研究进行了解,并采取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相关女性主义理论,从青蛇配角到主角身份的转变、青蛇形象的丰满立体化,以及女性同盟对抗男权意识三个角度对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重塑及其意义展开研究。
2. 从配角到主角:青蛇演变史
对比而言,传统《白蛇传》中塑造的青蛇则是以人性正面色彩的彰显更为突出,她对素贞忠心不二,也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类型化的忠仆形象,形象也较为扁平。为了对青蛇形象的重塑有纵向的深入了解,笔者也对《白蛇传》的发展做了初步的考证,对其中的青蛇的出现和人物角色身份定位做了溯源。
首先,“青蛇形象最早是在文本和民间的口头流传中被孕育出来的……只是一些雏形或者对后期形象发生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相关形象,而这种追溯,可从唐代传奇《李黄》起” [10]。《太平广记·李黄》被普遍认为是白蛇故事较正式的文本记载和发端,青白在此文中是毫无人性、没有具体定位的妖,其中关于小青原型的描写是:“青服老女,白衣之姨也”( [11], p. 436),此时小青是白蛇的姨母。
其次,在明清又有了很多与白蛇相关的衍生故事。在《湖壖杂记雷峰塔》( [11], p. 438)中,小青的原型是一条青鱼精,是白蛇的丫鬟;之后的《西湖游览志》、《小窗日记》( [11], p. 438)也同时提到了白蛇、青鱼两怪;《花朝生笔记》( [11], p. 440)中的婢女有了“秋鸿”这个姓名,也有了对白。
“明代洪楩的收录的宋话本《西湖三塔记》大约就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文的蓝本”( [11], p. 440)。白蛇身边出现了乌鸡精“卯奴”和而“皂衣婆婆”獭精两个仆奴角色,此处的“皂衣婆婆”和“卯奴”的结合则可以看作青蛇的原型,“卯奴”也被称作白娘娘的“女儿”。
而明代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2] 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的完整白蛇传说。文中的“青青”是一条青鱼精,也在结尾被收服,具有警世意义,这也是白蛇传的雏形;在此之后,从戏曲方面看,许仙、法海几个主人公都已完备,婢女也有了“小青”这个姓名。“《双断桥》以及方培成的《雷峰塔传奇》、《白蛇宝卷》、《义妖传》中的小青或青青都演变为蛇精形象” [9];在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中,婢女首次有了“青儿”的称呼 [10];在平剧戏目《双断桥》 [13] 中:“适许仙受法海金钵至,小青见之,怒甚,欲挥剑斩之”,小青拥有了更多性格面的展现,面对法海时正义感显露。而《义妖传》弹词又是白蛇传说中最详细的一种( [11], p. 443),小青在里面是青蛇精,和白蛇一样有了更多正面性和伦理化色彩。
由此归纳可以看出,小青的角色身份从白蛇的姨母、奴仆再到女儿、丫鬟,最后演变为姐妹,也从未知精怪发展到青鱼精、乌鸡精或獭精再到青蛇精。与此同时她的姓名也是从无到有的,从“青服老女”到“皂衣婆婆”或“卯奴”,再到“青青”、“青儿”,最后是“小青”。
从人物的功能性来谈,最初的小青只是作者一笔带过的角色,是主角的陪衬,单纯烘托白蛇又或助纣为虐,作者所用的笔墨甚少;接着小青成为了帮助白蛇许仙情缘牵线的功能性人物,例如红娘或者好姐妹,最后才被塑造成与白蛇平分秋色的,甚至是贯穿全文情节的主角。在白蛇传说的演变中,小青从几乎无性格的展现到性格扁平的恶毒精怪和帮凶,再到逐渐有了人性,帮助白蛇和许仙爱情时伦理化、正面化的形象;但在近代的大众白蛇传说中,她也只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下的忠仆义妖,人性的展现比较单薄。综上所述,从纵向来看,小青由身份、地位、形象、性格的模糊到渐渐成型有一个的过程,也是作为其配角的形象的体现。
而李碧华笔下的青蛇则从配角被塑造成了主角,同时也不仅仅是主角,而是小说的叙述者。她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有嫉妒、有爱慕之心,被真真正正的塑造为“常人”,不再只是一种符号。相比白蛇的完美无缺,青蛇的形象更加“接地气”,更具“人性化”的特点,也更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和共鸣,在读者心理起到反客为主的作用。
成为主导人物还表现在其行动和功能的变化中,小青的行动串联并影响了整个故事和主要情节,从嫉妒许仙——勾引许仙——姐妹反目——设计素贞——带回仙草——与许仙偷欢——争夺许仙——勾引法海——杀死许仙再到最后救出素贞、继续寻找许仙转世全部情节中,小青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也再不是之前那个没有对白和性格的丫头了;“相比近代婚恋型《白蛇传》,青蛇的形象开始摆脱单一的相助者角色,逐渐融合了辅助者、对手,甚至是角色中的‘异类’地位” [10]。此时她拥有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并与每个角色建立了不确定、不稳定的冲突和关系。“她可以是白蛇的丫鬟、姐妹,甚至情敌、恋人,也可以是许仙的通房大丫头、小妾,甚至情人” [10],甚至与法海都产生了一层暧昧关系。由此可见,李碧华笔下的青蛇突破了以往传说中类型化人物的塑造,成为了人物性格复杂而立体的圆形人物,变得更具现代女性气质,实现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身份转变。
3. 兽性、人性和妖性的结合
李碧华的《青蛇》在叙事上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也突破了传统《白蛇传》中作为配角的青蛇形象的模糊性、扁平化特性,使其具有了更多的反叛色彩;作为主角的青蛇由蛇——人——女人的发展历程完整地表现了其复杂的性格特点。在从配角主角化的过程中,她的性格可以说是“人性”与“妖性”、“兽性”的复杂交织,也经历了一个从遵从到反叛的过程,这也展现了她作为主角的人格多面性。兽性是欲望的呈现,人性表现为做人的渴望,妖性则是对人世规则的反叛。笔者也将对青蛇分别从兽性、人性和妖性的结合三个角度的反叛性展开论述,挖掘其性格变化的深层内涵。
在《青蛇》中,李碧华以第一人称叙事使小青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和叙述者,这也使其性格的变化历程可以更为直观、完整得展现出来。在文本中,小青是修炼一千三百多年的蛇妖,因此她的性格中有较多蛇的兽性,而白素贞修炼了近两千年,与“得道成人”的境界更进一步,对人性也有更多的向往和学习,从这一方面来说她更像真正的“人”。兽性是生物最原始、最直接的欲望表达,小青天性不拘、天真自在,无论是初化人形时对人直着身子走太辛苦的抱怨、最大的快乐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的简单,还是对姐姐为何用花香来掩盖腥气涎液( [14], p. 4)的不适都体现了作为生物最原始的需求和动物性。
“刚打个呵欠,空中有只苍蝇,自投罗网,长舌一伸,先来个小点。吃过苍蝇,一得意,翻翻白眼,尖锐的长牙又露出来”( [14], p. 28)。
这一段描写也可以说是她作为“兽”的“蛇形毕露”之作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小青未入世时的需求大部分着眼于吃喝睡的较低层次,在高级需求上还没有过多关注。而在入世之后对爱情的体验和作为女性想求得男性关注和爱慕的心态则是归属感需求和尊重需求层次的反映。需求层次的递进代表了人的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小青做“人”后的正常心理变化,以及“兽性”被“妖性”和“人性”压制的体现。
未入世之前,小青的世界简单纯粹,她的想法比蛇更深,又比人更浅,与其说她是蛇,不如说她更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对人生和世界观有自成体系的独到理解,这便是她其兽性和人性交织的一点。
“不。我日夕夜想自己何以与别不同,已经很忙”( [14], p. 5)。
“西湖本身也毫无内涵,既不懂思想,又从不汹涌,简直是个白痴”( [14], p. 1)。
“人都爱挺身而出,瞎勇敢……这‘脚’!还有十只没用的脚趾,脚趾上还有脚甲,真是小事化大,简单化复杂!”( [14], p. 5)。
受白素贞想做“人”的影响,入世之后,小青对人性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由好奇到失望的过程。吃下了吕洞宾的七情六欲丸,小青才真正情窦初开、渐渐有了情感和人性。
“我还不是一个女人,我有不可思议的不安定”( [14], p. 58)。
可见在小青的心里,也有想当女人的渴望和冲动,随即诞生了她为证明自我魅力、和素贞攀比的“勾引”行为。
妖性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下的“人”的规则的反叛和对个体本真的坚持。大众视野下的蛇妖被赋予了妖媚多姿却惑人心智的形象。青蛇对许仙、法海的勾引诱惑和直接的欲望表达,是不受人类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的。相较于白素贞到人间只为了找个平凡男子结婚,学着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而小青则是出于寂寞相随其来到人世。在人类情感体验的过程中,小青最初因嫉妒和好奇萌发了对爱情和男人的探索欲,因为对白素贞的依赖和崇拜,她也受到了其努力融入人类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地对许仙、法海产生了欲望,也对“做人”的苦乐有了更多评判;但李碧华笔下的青蛇却大胆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对女子的约束,她偷银子、贿赂官员、勾引许仙、背叛姐姐,还利用蛇妖的性感魅力诱惑法海,这些都是其妖性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反叛性和无规则意识的体现。
看着素贞爱上了许仙,或出于嫉妒和羡慕,小青自己也难逃情劫,对许仙产生了情感。在许仙背叛了素贞时,她又对人性产生了愤怒和失望,人世的爱情背负了太多枷锁,也充满了欺瞒和背叛。初为“人”,小青俨然不如素贞陷得深。传统伦理道德下的人性包含了理性、伦理束缚和对人世规则的遵从,它要求素贞做一个“三从四德”、“以夫为天”的合格妻子,而又因为“人妖殊途”的规则而要把她置于死地。小青没有像素贞那样“像人”,因此她人性的显露也更具现代性的开放和反叛色彩,较多地听从于内心和感情而不在意规矩,与许仙的“偷情”也更具“妖性”作风,所以她比起素贞所受的伤害也更小。但人性的复杂也是深不可测、难以揣摩的,它的幽暗、善变在青白被许仙背叛时完全显露,姐妹间也有过因情生妒而互相伤害,小青看着怀孕的素贞时,才明白了人世间爱情的痛苦,也认识到了做“女人”的卑微,正如素贞所说的:“人间的规矩,是从一而终”( [14], p. 69)。与小青未做“人”时无拘无束的那句:“我不喜欢规矩。最讨厌了: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 [14], p. 59),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小青人格中“人性”和“妖性”的矛盾交缠也达到高潮。
在兽性、人性和妖性的结合中,小青的性格更加丰满和立体化,比起传统文本中的丫头形象也更生动活泼。从兽性到人性、妖性的层层递进以及三者交相融合的过程中,小青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性格鲜明、独具魅力的女性。李碧华想借此塑造的是一个被拉下“神坛”的女性,并且展现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如果说素贞是完美无缺的“神”,那么小青就是一个更接地气的“人”,可以让读者从现实生活中每个小人物身上找到她的影子。
4. 女性同盟对抗男权意识
青蛇从“兽”发展到“人”的阶段也就拥有了更为强烈的男女性别意识,也从“人”逐渐过渡到男权社会建构下的“女性”性别身份,并且开始了对“女人”这种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的反叛,女性主体性的体现也越来越强烈。笔者将从正视情欲是女性的正当需求、以同性恋对抗异性婚恋两个方面谈青蛇被赋予的激进的女权意识。
4.1. 女性对情欲的反叛
蛇女形象自古与情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初从远古开始就有蛇的图腾崇拜和一种原始生殖崇拜;到了父系社会之后,蛇女被赋予了利用美色害人、吸人精血的恐怖妖精形象,也是男性为了打压女性地位的表现。此时美艳动人的蛇女形象也同时具有“女子美色对男权社会有了服务性功能 [5] ”,充满了情欲色彩,这也暗示了男性对蛇女形象无限的压制和贬低、意淫和想象;第三个阶段的蛇女形象开始向伦理化过渡。例如《白蛇宝卷》中的白蛇则有了生子情节 [11],这也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生育功能的重视,将情欲与生育挂钩。因此蛇女形象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从原始崇拜——消解女性生殖崇拜:情欲化蛇女形象——保留情欲化:向伦理化过渡三个阶段,可见传统白蛇传说中建构的青白二蛇形象充斥着男性的理想化诉求。而李碧华笔下青蛇则是情欲化的,这种对情欲的正视甚至放纵是对久处于男权社会底层的女性的某种反叛和自我追逐,展现了女性意识的崛起。
情欲是贯穿小说的核心,男权主义者眼中的女性只是承受情欲的一方,而在性关系中不具备主动性,但在李碧华的笔下,女性成为了情欲的主动参与者,其情欲在这里也是合理的。首先她安排了吕洞宾的七情六欲丸情节为借口,让青白二蛇不用再承担红颜祸水的污名,因此她们的情欲色彩也被合理放大,爱情也因欲望而起。李碧华利用了这一情节摆脱了传统男性加在女性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使青蛇形象更具现代女性的反叛和开放自由意识,不再压抑欲望,也使情欲书写合理化、正常化。
反叛具体表现在主动勾引姐夫许仙,以及原本与法海无感情线的小青在小说里色诱法海两个方面。关于小青与法海、许仙的情色场面的描写是对传统白蛇传的大胆突破,也对青蛇形象有了更多重的塑造。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性力”或“原欲”是弗洛伊德本能学说的核心概念,也是给人们的全部活动、本能、欲望提供动机的力量( [15], p. 253)。青白二蛇入世的故事由情欲展开,白蛇爱许仙一半也是因为“色”,小青对法海和许仙的欲望也没有因身份退却,人和人、人和妖的界限被情欲模糊了;此外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按‘至善原则’活动……自我作为中介,便不得不处在本我的驱使、超我的谴责、现实的限制的夹缝”( [15], p. 190)。小青本我的欲望因七情六欲丸得以释放,所以在现实社会中自我才会受情欲驱使做出勾引许仙的行为,但当白蛇告诉自己已经怀孕时,她的超我在一定程度被激发,良知和道德使她放弃了和素贞争夺许仙,使自我和本我得以压制。
但青蛇对于勾引和情欲大胆试探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传统小说中对女性贞洁观和情欲主动权的壁垒,青蛇已经对情欲进行了大胆反叛,也显示了女性观念从顺从到反叛的过程。
4.2. 由异性恋到同性恋的书写
传统白蛇传说中的男女爱情被作为佳话典范永世流传,白蛇和许仙的爱情突破了法海的阻碍,人妖的限制,超越了生死和种族的界限,也是经典的异性恋爱情模式;而李碧华则通过对爱情的反叛为我们展示了社会中男女的权力斗争和男权的绝对压制。
关于爱情的输赢我们却无法定论,但在四人情感的纠葛中,许仙俨然高明得多。他心安理得享受素贞的付出,却又生异心想占有小青,在此同时得到了法海的青睐,法海也开始对许仙施以“勾引”手段。当爱情突破男女两性,延伸到同性之间,其对立意味就浓烈得多。李碧华说过这是一个勾引的故事,无论是传统的许仙白蛇的爱情还是小青对素贞的暧昧之情,法海对许仙较显突兀的暧昧和占有欲,都把我们指到一个新的方向。笔者认为,《青蛇》中的同性情结也是女性对男女爱情以及男权社会的失望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法海对许仙的感情也是对男性力量团结起来对女性施以绝对的压制现象的隐喻和暗示,这也将女性在爱情中的卑微和弱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传统社会对同性恋视为洪水猛兽,而青蛇对白蛇的暧昧感情也是对传统异性恋社会伦理的反叛和突破,李碧华所说的“素贞勾引小青”也从多处描写反映出来。
“小青”她真心地说,“此刻我只有你!”她终于觉悟了( [14], p. 125)!
“姐姐”,我扶持着她:“我们索性把姓许的忘掉吧。——要一个‘父亲’来干啥?我们自己把孩子提携。忘了他吧”( [14], p. 125)。
男人爱女人,也是在一段特定的日子里罢了( [14], p. 130)。
此时两个女人又绞缠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的新欢。直到地老天荒( [14], p. 145)。
青蛇对白蛇的同性暧昧,青蛇对许仙的勾引与刺杀,法海对许仙的占有欲,同性之恋、多角之恋、佛妖之恋都是对传统的白蛇许仙的天作之合良姻模式的反叛,它们夹杂欲望却超脱性和伦理的范畴,更多显示了李碧华对于传统社会性别建构的突破和对《白蛇传》传统异性恋主题的反叛。蛇妖因其身份的特殊可以打破固定的社会性别的符号,突破男权社会对女性伦理和性别固化的限制,女性不止可以喜欢男性,起码在“人性”复杂的青蛇这里是随性而自由的。
根据性别的社会建构论来看,“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认为虽然男女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由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16]。青蛇和白蛇的社会性别虽为女性,但合理地说作为本体“蛇”而言她们是“雌性”。因此青蛇受人类社会影响的性别建构就表现出了不稳定性、非固定性,当青蛇在人类社会中体会到女性性别、身份角色的卑微和压抑时,她对于白蛇的同性恋倾向也更加强烈。性别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人生而为男女都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 [16]。男人和女人的身份认定是潜移默化的,不止受限于生理性别。青蛇学习做“女人”是主动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但随着其在人世的“成长”愈发加强的同性恋倾向也是对于男性霸权和异性恋霸权的反叛和解构,也是其作为“蛇”的自然情感。古代社会对男性的包容更体现在对男同行为的包容上,帝王和达官贵人好男风正常,而女性不然。可见,李碧华的书写不止是对人物性别的模糊,也是对“人性”模糊。情感的复杂打破了白蛇传说中单一的爱情叙事模式,人性的复杂使男女权力得以颠覆和解构。
综上可见,青蛇分别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姿态明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卑微和依附,并通过自身行为的反叛加以对抗。小说的主题以及男性形象的异化也带有明显的批判性,作为男性的许仙和法海带有明显的阴暗面和负面色彩。许仙被塑造为虚伪贪婪自私,贪生怕死,多次背叛素贞和小青的负心汉;法海则霸道专断,表面上强势地维护人世秩序,背后却私心想占有许仙,满嘴佛法道义却被小青扰乱了修行,同时法海也代表了男性和人类的权威,对女性和妖施以压制。李碧华以自己的女性意识改写了神话传说,许仙和白素贞美好团圆的爱情大结局竟是一场镜花水月,男性形象的异化也充斥着男权社会的伪善和夫妻恩爱的假象,讽刺意味强烈;青蛇更是被作者赋予了激进的女权意识,例如正视情欲是女性的正当需求、由同性恋对抗异性婚恋等,借此颠覆其中浓重的男权控制。
5. 结语
受女性主义的影响,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重塑是对传统男性创作的反叛,此时青蛇进入了男性话语体系中,颠覆了男性视角下的归于伦理化的蛇妖形象。在开始对许仙动情时,青蛇就当他是“猎物”,而在认清了许仙的背叛和伪善之后,对许仙的“刺杀”行为也标志着女性对男权的彻底颠覆,饱含女性解放的色彩。李碧华重塑青蛇形象,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传统角色的女性主义观照,从女性视角凸显青蛇的女性主体意识,彰显当代女性价值观。
《青蛇》故事的悲剧性也在于李碧华发掘了女性在爱情中的性格弱点:痴情、容易迷失自我。沉溺于爱情泡沫里的白蛇无法用贤良恭顺换来真心和美满结局,到最后面对男性时只能低到尘埃里。在镇压几百年后白蛇遇见轮回的许仙时也义无反顾,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看似清醒的青蛇也一改对许仙的憎恨和失望,在经历复杂的内心斗争后还是选择向爱情和欲望编织的幻影走去,这也折射了现代女性面临的爱情谜题和现实境况:被男性、第三者、孩子束缚的现代女性面对感情变质时抗争的无力和软弱性,对当下女性具有反思悲剧命运的现实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社会下,大众的审美风尚发生改变。李碧华对《白蛇传》的改写由青蛇这个反叛的、有情有义的、敢爱敢恨的“坏女人”形象为主体,展开了从爱情到情色主题的转变,借此探讨现代女性的爱情观。在这方面青蛇白蛇同而不同,她们分别代表现代社会的两类女性,虽然有反叛性却都受制于男权社会的性别建构。以自己的女性意识改写神话传说,颠覆其中浓重的男权控制,正视女性的自我欲求,这是作者在作品中经常运用的方法,比如《潘金莲》、《川岛芳子》等作品都有替女性发声的独特视角,表现了李碧华重写历史、反抗男权书写的姿态。她的小说也不仅仅局限在女性意识上,而是具有人性和家国的视野,借历史和传说喻今,也更深层地思考了处在现代国家、社会中的人性和命运的走向,境界宏大。
在现代社会中《青蛇》也更符合香港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在当时众多武侠小说、玄幻小说充斥下,《青蛇》是一部娱乐化、迎合市场的写作。受20世纪80、90年代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李碧华对青蛇的形象重塑一定程度上是对崇高审美的消解,它反映了现代人对自由、个体、游戏化、娱乐化故事的追逐。男性视角下贤良淑德、悬壶济世的白娘子被大胆叛逆、放荡不羁的青蛇掩盖了色彩,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和男女爱情典范被打破,传统话语中的崇高道德情操也逐渐被青蛇形象消解,李碧华通过消解理性、教条来探讨传说,通过对脱离现实、走向定型化的传说故事的反叛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审美层次。
文章引用
李亚萍,闫月宁. 论李碧华对青蛇形象的重塑
Study on Li Bihua’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Green Snake[J]. 世界文学研究, 2020, 08(03): 103-11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0.83018
参考文献
- 1. 张衡. 经典传说解构中重塑女性形象——以李碧华《青蛇》为例[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0(4): 440-442.
- 2. 韩旭东. 论《青蛇》的性别视点与女性主义色彩[J]. 梧州学院学报, 2016, 26(2): 60-64.
- 3. 严虹. 颠覆与重构——评李碧华小说《青蛇》[J]. 文教资料, 2008(3): 32-34.
- 4. 侯春慧. 白蛇传奇与现代体验——以李碧华小说《青蛇》为中心看一个传说的流变[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8(1): 72-75.
- 5. 张万丽. 《白蛇传》青蛇形象的流变及演绎初探[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2008.
- 6. 白杨, 杜未未. 原型的嬗变与新生: “故事新编”中的“青蛇”形象[J]. 文艺争鸣, 2016(12): 105-110.
- 7. 聂焱. 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历史家国意识[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2006.
- 8. 高艳芳. 青蛇论[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9. 焦丽君. 浅析“青蛇”原型及在戏剧作品中的嬗变[J]. 戏剧之家, 2014(10): 29+52.
- 10. 古佩冲. 从青蛇形象流变探析文学史中“配角主角化”现象[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 11. 谭正壁. 三言二拍源流考(上卷)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2. 冯梦龙. 警世通言[M].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 13. 中外书局: 古今戏剧大观(第六册) [M]. 上海: 中外书局, 1921.
- 14. 李碧华. 青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15.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6. 豆瓣. 女性性别的社会建构论[EB/OL]. https://www.douban.com/note/620511241/, 201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