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Vol.
09
No.
02
(
2021
), Article ID:
41408
,
9
pages
10.12677/OJLS.2021.92036
已撤销的商事仲裁裁决域外“复活”问题探究
温顺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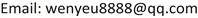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21年1月25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22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31日

摘要
根据传统仲裁理论以及国际主流观点,仲裁裁决一经仲裁地法院撤销即已宣告该裁决“死亡”,因而也无法获得执行地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但是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衍生出了一系列国际商事仲裁的新理念、新理论和新动态,如意思自治在国际私法领域的扩张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理论的更新等,进而导致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重获新生。但是由于该现象依然处于缓慢演进状态且各国国情差异较大,故而在“复活”规则方面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致使现行的国际商事仲裁执行秩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受到干扰。针对此问题,本文在分析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复活”法律依据的基础上,从国际法层面和国内法层面提出相应的完善规则。
关键词
已撤销商事仲裁裁决,“复活”规则,自由裁量权
A Probe into the “Resurrection” of Cancelle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
Shun We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Jan. 25th, 2021; accepted: Feb. 22nd, 2021; published: Mar. 31st, 202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arbitra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view, once the arbitration award is revoked by the court of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award is declared “dead”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recognized and enforced by the court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rbitration is executed. However,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 series of new ideas, new theories and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ve been derived,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autonomy of will in the field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pdate of the arbitrati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rebirth of the arbitration awards that have been cancelled. However, because the phenomenon is still in a slow evolution state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large, there is a lack of uniform applicable standards in the “resurrection” rule,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stabil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execution order. In view of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basi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cancelled arbitral awar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erfect rul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Keywords:Cancelle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 “Resurrection” Rule, Discretionary Power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本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以及承认与执行制度是仲裁地国与承认和执行地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双重监督,也是国家权力介入仲裁这种民间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途径,因而通常被人们视为判定该国仲裁法制完善程度的标尺。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仲裁裁决之撤销与执行的效力具有差异性,即撤销仲裁裁决具有普遍效力,因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便不再具有效力,其他国家应当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然而,这种传统观点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遭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挑战,即如法国、美国、荷兰等国依据本国国内法执行了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于是,在传统仲裁理论语境下,已经“死亡”的仲裁裁决出现了“复活”现象 [1]。这一现象已经产生便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也引发了对各国针对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能否在域外“复活”的关注,即若支持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具有域外“复活”效力,则其法律依据为何,应当以何种法律标准予以严格规制。此外,若允许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复活”是否会对《纽约公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造成冲击等。反之亦然。虽然加入《纽约公约》至今,我国尚未遇到已被撤销的外国仲裁裁决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案例,但是出现过已被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于2006年由当事人向德国柏林地区高级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案例 [2]。随着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程度不断加深,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因此,基于上述缘由,对于已被撤销的上述仲裁裁决的域外“复活”问题不可不察。
2. 相关国家关于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立法与实践
2.1. 法国的立法和实践
法国《新民事程序法典》第1502条规定:“法国法院仅因以下原因方能拒绝承认与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仲裁员在没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作出裁决,或者裁决是基于无效或业已超出有效期的仲裁协议而作出的;仲裁庭的组成不合法,或独任仲裁员的任命不合法;仲裁员超越权限作出裁决的;仲裁程序缺乏公正性的;承认与执行将违背国际公共秩序的 [3]。”显然,在该法典中,法国并没有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列入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因而在实践中,当涉及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时,法国通常采取有利于仲裁裁决“复活”为要义。例如,在Yugoslavia v. SEEE (France)案中,在瑞士法院宣布涉案的裁决并非仲裁裁决后,胜诉人SEEE依然向法国申请承认与执行该裁决时,法国里昂上诉法院依旧裁定准予执行。再如,在Pabalk Ticcaret Sirketi v. Norsolor S. A.案中,在奥地利法院以仲裁庭越权仲裁为由部分撤销该裁决的情况下,当胜诉方当事人向法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时,法国最高法院依据《纽约公约》第7条的“更优惠权利条款”准予执行,并指出,执行地法院有义务按照本国法决定是否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而非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此外,在1993年的Socittt Polish Ocean Line v. Socittt Jolasry案中,法国法院依据本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作为准予仲裁裁决执行的依据 [4]。此外,在Socittt Unichips Ftnaniiaria v. Gesnouin、法国公司(S.A. Lesbats et Fils)/德国公司(Esterer WD GmbH)仲裁案以及“印度尼西亚公司/法国公司仲裁案”(2007)等案件中,法国法院均执行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从法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其“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司法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其“复活”法律根据也多与本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和《纽约公约》第7条“更优惠权利条款”挂钩。显然,这与法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解密切相关。法国推崇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内国化”理论,主张国际商事仲裁独立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因而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按照本国立法,而不必顾虑仲裁地国对裁决的态度。同时,法国坚持将《纽约公约》第5条理解为授权性条款,在此基础上搭配《纽约公约》第7条“更优惠权利条款”的适用,赋予国内法更为优先适用的地位,从而复活本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2.2. 美国的立法与实践
《美国联邦仲裁法》第201条规定:“1958年6月10日签署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应由美国法院按照本章予以执行。”第202条规定:“属于公约管辖范围内的仲裁协议或裁决,无论契约或非契约,凡是产生于法律关系的仲裁协议或仲裁裁决,并被视为包括本法案所述的交易,契约或协议在内的商事性质者,均属于公约管辖范围。产生于这种关系的仲裁协议或裁决,但完全系美国公民之间者,则不应视为公约管辖范围,除该关系涉及国外财产,履行或执行将来在国外进行,或与一个或多个外国有某种其他的合理联系者不在此限。根据本条款,如果一个公司设在、或其主要营业地在美国,则该公司法人系美国公民 [5]。”
从美国上述立法来看,其对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美国是否具有复活可能性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立法态度,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一套独立的判例认定体系。
据统计,美国法院目前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e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例共计8个,其中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有2个。
1996年的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案是第一例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实现“复活”的案例。在该案中,法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明确了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即法院据此可对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作出支持或拒绝的裁决。然后,法院继续援引《纽约公约》第7条,认为《美国联邦仲裁法》是更优于《纽约公约》的国内法,在该法中并未明确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可作为拒绝执行申请人申请的法定理由。最后,法院指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一裁终局的约定构成了法院承认与执行该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约定事由。同时,法院在判决中还对国际礼让原则进行了阐释,认为:“没有国家会持续地承担执行对国内法院有基本偏见的外国利益的义务,礼让从来不会迫使国内法院忽视本国公民或者他国公民根据本国法享有的权利。”
在Corporatio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 L. De C. V.一案中,美国法院对该仲裁裁决的撤销理由进行审查后,认为墨西哥法院的撤销裁决适用的是仲裁开始后才生效的法律,因此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违背可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因而该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符合拒绝承认与执行的例外条件,法院可准予执行申请人的执行申请,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在其他和后续的案件中并没有延续上述的“复活”路径,在1999年的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一案中,美国法院根据如下要点作出拒绝该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复活”裁决:1) 援引国际礼让原则;2) 指出案件与美国不存在紧密的连结因素;3) 尼日利亚撤裁程序内容合法,美国法院没有理由行使《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在Martin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hnica. S.p. A.一案中,美国法院除了强调撤裁法院属于合法撤裁且该案件与美国无涉外,还特别指出了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的终局效力。在Termorio & Leas Co. Group S. A. E. S. P.v. Electranta S. P., et al.一案中,美国法院对《纽约公约》规定的首要管辖权和次要管辖权进行了简要阐述,指出首要管辖国之撤裁裁决具有确定之效力,作为次要管辖国的美国不应轻易否定首要管辖国合法作出之裁决。此外,法院还强调,美国奉行的有利于仲裁的政策不能成为该仲裁裁决“复活”的充足理由。在2014年的Thai-Lao Lignite (Thail.) 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与2017年Getma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Guinea案中,美国法院除了考虑上述裁判要点外,还特别强调严格限制法官对《纽约公约》第5条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认为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方可适用,即只有仲裁地国之撤裁裁决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观念,法院才会考虑“复活”该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从对上述案件的分析来看,美国法院决定是否“复活”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因素,主要包括《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第7条的“更优惠权利条款”、明显违反公平正义的例外情形、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裁决效力约定、区分首要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下的国际礼让原则、案件与美国是否具有紧密的连结因素。当然,最后一点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其有地方保护主义之嫌。因此,总体来说,美国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决定已撤销仲裁裁决是否复活的法律标准,即以拒绝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为原则,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为例外。
2.3. 中国的立法与实践
根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规定,如果被执行人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公约第5条第1款中第5种情形之一,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该款明确排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我国明确将《纽约公约》第5条界定为强制性条款,这断绝了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我国法院“复活”的可能性。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送审稿)》第36条规定:“外国仲裁裁决尚未生效、被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经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上述观点也得到确证。
同时,我国相关法律对《纽约公约》第5条与第7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厘清,有学者认为这可以为中国未来确定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能过“复活”提供切入点。否则,我国将会面临以下司法难题:若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之理由与我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理由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如果一味地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与国家司法主权不符,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在司法实践方面,我国法院目前还没有遇到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向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情况。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曾出现过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又被当事人于2006年在德国柏林地区高级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例。此外,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相关也有一例,即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在该案中,广东省高院以《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戊)项裁决尚未对当事人生效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但最高院复函并未对(戊)项的理由作出回应,而是以(丁)项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 [6]。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法院遇到类似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情形也会增多。
3. 学界对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态度
对于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域外复活现象,由于《纽约公约》的模糊性的规定,在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各国的立法与实践中也呈现不同的样态。
在对待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域外“复活”对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理论及实践所造成的影响的态度上,学术界主要存在支持、反对和折中三种。
3.1. 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之肯定论
支持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学者指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可以“漂浮”,不受仲裁进行地国法律的限制 [7]。换言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已摆脱仲裁地国之束缚,仲裁裁决最终能否获得承认与执行与作出该仲裁裁决的仲裁地国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而仲裁地国法院对该仲裁裁决所行使的撤销权不应成为该仲裁裁决在域外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司法阻碍,除非该裁决构成《纽约公约》项下规定的撤销理由,不然域外执行国应当忽视由仲裁地国作出的撤销裁决。同时,该派学者主张,《纽约公约》的中文版本、英文版本、俄文版本和西班牙文版本在对第5条进行规定时均使用了表示“可以”(may)的措辞,以及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宗旨解释等方面对该公约第5条进行解释,都可以得到公约赋予执行地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结论 [8],由此执行地国法院对于被撤销仲裁裁决是否承认与执行具有自由裁量权,而不必然受制于仲裁地国的撤销行为。该派学者还指出,仲裁裁决即使被撤销依然能够“存活”,理由在于仲裁裁决并非建立于仲裁地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当事人仲裁协议的基础上 [9]。此外,该派学者还从国际礼让原则出发,论证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依然能够被执行地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并不违背国际的司法礼让,而恰恰相反的是,过多信任仲裁地法并赋予仲裁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的普遍效力将会增加司法不公的风险 [10]。因此,从支持方的观点来看,其主要基于《纽约公约》第5条的规定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具有的自主性出发,即一方面《纽约公约》第5条赋予了执行地国法院是否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采纳“非内国裁决理论”和仲裁意思自治理论,强调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而非仲裁地国。
3.2. 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之否定论
反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观点认为,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于仲裁地国,已撤销的裁决不具有可执行性 [11]。《纽约公约》不能成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因为该公约指向的对象是有效的仲裁裁决,而不包括已被仲裁地国撤销的仲裁裁决。同时,对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执行地国的单边决定,是对外国仲裁裁决的过渡管辖 [12],既是对外国判决既判力原则违背,也是对国际礼让原则的侵犯,由此可能加剧了仲裁地国与执行地国的矛盾,不利于两国开展国际商事交流与司法交往。另外,由于不同执行地国对仲裁撤销理由作出不同的规定,若承认被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的效力,可能致使《纽约公约》的适用陷入不稳定状态,不利于维护《纽约公约》具有的统一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适用标准。具言之,若允许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域外“复活”,则可能会出现该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某一执行地国获得承认与执行,而在另一执行地国却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相互冲突的司法状态,因此,将会破坏《纽约公约》适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3.3. 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之折中派
折中派的观点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绝对化和僵硬性倾向,不符合现代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发展。因此,该派学者Roy Goode认为,原则上应尊重仲裁地国法院关于中止或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以避免因程序多样化造成的不一致判决的成本、不方便和风险,能够促进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合作,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形,比如法院的判决是通过欺诈获得的 [13]。另外,Chan也指出,法院应当将已撤销的外国裁决推定为不可执行,并且应承认外国法院的撤销决定,除非有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外国的撤销决定是任意的或明显错误的,或者是由欺诈获得的,程序明显的偏见或者不公或者根据与法律的正当程序不相容的程序获得的 [14]。
对此,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观点分野,例如,以张美红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我国应对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持开放态度,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对此问题一贯持否定态度过于机械、僵化,不利于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15]。以谢新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否认《纽约公约》第5条为执行地国重新“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提供依据 [16]。
由此,在关于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能否在域外“复活”的问题上,在学界依然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究其缘由,在于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来源的不同理论主张以及对《纽约公约》第5条存在的认识差异。因此,要回答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域外“复活”效力问题,还应厘清上述理论分歧和深入分析该公约的相关条款。
4. 已撤销仲裁裁决“复活”现象缘起与现行“复活”规则缺陷
4.1. 已撤销仲裁裁决“复活”的背景理论考察
对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现象的考察应当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进行,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促进国际民商事交流的深度交融,相应的,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发生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变革在某些领域或开疆拓土,或调整战线。在法律适用领域,前者如意思自治理论由最初仅适用于合同领域到现今扩张至侵权、物权和婚姻家庭等领域。后者如“法则区别说”、“比尔规则”逐渐被摒弃,最密切联系原则隆重登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不断突破原有的适用边界;二是国际商事交易主体自由权利的扩张。前者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方面出现了允许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排除仲裁地国法院行使撤销权的立法 [17]。例如,2011年修改的法国仲裁法令第152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特别约定放弃对裁决提起撤销之诉。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规定中的“当事人”并没有国籍限制。同时,瑞典、比利时等国在各自的仲裁立法中也作出类似规定。此外,有些国家另辟蹊径,在司法实践中允许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扩大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情形。比如,美国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一般局限于程序性事项,但在实务中法院依然认可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约定实体事项的可审查性的做法。在Gateway Technologies,Ine.诉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 案和 Lapine Tecnology Cor.诉Kyocera案中,美国法院均认可当事人通过协议将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由程序问题扩大到实体问题 [18]。推动意思自治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扩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受到仲裁自治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国内立法、司法实践和相关国际公约的支持,同时还离不开“友好仲裁”理念的固守。
第二方面即国际商事交易主体自由权利扩张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主要表现为,在各个经贸领域受到国家强行法的限制越来越少,同时可以自由地进行跨国投资和跨国贸易、自由约定跨国交易合同内容、自由地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等 [19]。在国际商事交易主体自由权利不断扩张的前提下,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可以自由选择仲裁程序法、自由约定不受仲裁地法院司法审查(即约定“一裁终局”,排除仲裁地法院行使对仲裁裁决的撤销权),这一点在法国和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此外,当事人还可以约定将该司法监督权交由执行性地法院行使等。上述做法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已“死亡”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重新复活。
4.2. 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现行规则缺陷
如前文所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已撤销仲裁裁决域外“复活”效力已经成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一个真实现象,是国际民商事交往当事人及各国学界、实务界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我们审视现象时,发现其无论是国际法层面还是国内法层面均存在相当的制度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国“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复活”法律标准。例如,法国的“复活”依据主要包括《纽约公约》第7条“更优惠权利条款”、《新民事程序法典》第1502条等。而美国的“复活”依据包括美国《联邦仲裁法》、当事人排除任何救济的仲裁协议、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国际礼让原则、当事人与美国是否具有紧密的连结因素、纽约公约第5条和第7条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一是在国家主权原则下,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实际制定相应的国内法,行使各自的司法管辖权,进而在撤销仲裁裁决理由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二是各国在对待仲裁自治的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别。
第二,《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缺乏明确性。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有些判决可以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和第7条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也可以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的规定拒绝让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复活”,前者如1996年的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案,后者如2017年Getma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Guinea案,由此造成了实践的混乱,影响了公约的统一适用。究其缘由,在于《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该条规定,被申请人与执行管辖机关可以(应当) (“may”)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第5项理由为:“……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中止执行。”有关缔约国对该条中采用的“may”措辞存在较大分歧,即若将该措辞理解为“可以”则承认执行地国法院在是否拒绝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问题上具有自由裁量权,若是将其理解成“应当”,则该条款为强制性条款,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将永无“复活”之日。
此外,《纽约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此条款又被称为“更优惠权利条款”。但是该公约对该条款中的“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并未作出明确解释。根据该条款,若作为缔约方的执行国参加的相关多边或双边协定,或者该缔约国的相关国内法对执行仲裁裁决更为有利时,则它们获得较《纽约公约》更优先适用的效力。换言之,如果执行国所签协定或条约,以及国内法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并不涵盖裁决已被撤销或中止的情形,则执行国法院可以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 [20]。由此,在各国发展水平和立法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相关法院把握“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尺度不一,进而加剧了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复活”规则异化的风险。
第三,同一国家缺乏统一适用的“复活”规则。在实践中,无论是强烈支持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复活”的法国,还是有限度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美国,都没有在本国的立法或判例中确定统一的“复活”标准和规则。换言之,各国在“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而定。同时,各国法院也未就同一“复活”判例的依据之间进行重要性排序和规定适用的逻辑先后顺序 [19]。出现该问题的理由在于:第一,每个案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很难建立一套统一的适用标准;第二,当前成功“复活”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案件较少,还不足以建立一套体系严密完整的“复活”规则或判例法;第三,各国为灵活把握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复活”尺度,以维护本国利益,也不愿意制定硬性的“复活”规则。
5. 已撤销仲裁裁决“复活”规则完善
5.1. 国际法层面的规则完善
鉴于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加入《纽约公约》,这就为我们在国际法层面对已被撤销的的仲裁裁决“复活”规则的完善提供了着眼点。换言之,从国际法层面完善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复活”规则,我们应当从现行的国际法即《纽约公约》着手,一方面立足于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契合国际立法经济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以该公约为切入也较容易为各缔约国所认可。
具言之,针对《纽约公约》第5条的模糊规定给各缔约方造成司法实践上的困扰问题,即由于该条款作为授权性条款抑或强制性条款的界定不清,不同的缔约方根据本国利益出发自行界定,从而决定拒绝/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造成了该条款适用的随意性或不规范性,也严重威胁以《纽约公约》为基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鉴于此,应当对该模糊条款进行修正,可以参照其他国际立法如以议定书的方式对《纽约公约》第5条中英文措辞“may”作出明确的解释。对此,笔者主张宜将其解释为授权性条款,因为无论是基于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各国“复活”现象的客观存在事实,还是从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都应当赋予执行地国对该裁决进行司法判断的自由裁量权。此外,为了增加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复活”规则的确定性,还应当借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9.1条,在《纽约公约》第5条中明确列举出缔约国可以撤销裁决的理由,以便为执行地国提供不予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清单。另外,针对《纽约公约》第7条中没有清晰界定“仲裁裁决任何权利”边界,造成了同一裁决不同执行结果的问题。《纽约公约》第7条可以明确:在申请人就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向多国申请承认执行时,申请人享有的仲裁裁决的权利以执行地国法律共同或相似的规定为准,以实现执行结果的统一性。
5.2. 国内法层面的规则完善
考虑到从国际法层面对相关条款的完善短期内难以达成、当前多数国家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能否“复活”的问题上尚存诸多顾虑和疑惑以及同一国内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统一可适用的“复活”规则等多重因素,因而有必要在国内法层面完善“复活”规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各缔约国的国情不同,因此想要制定一套完全相同的、非常具体明确的“复活”规则并不具有可行性。为了维护国际商事仲裁承认与执行秩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有学者主张可以考虑从执行地国的角度出发,在各执行地国的国内法中就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制定具有优先适用顺序的一般的“复活”规则 [19]。
对此,笔者认为是合理的,纵观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重新“复活”的案例,都反应出执行地国在决定“复活”该裁决过程中既具有客观现实条件,即作为涉案财产所在地等,又具有司法主动性,即可出于维护司法主权、维护本国公共秩序以及维护本国公民利益等需要出发“复活”本已“死亡”的仲裁裁决。在此基础上,在“复活”规则上应分三个方面进行设计:第一,顺应意思自治与当事人缔约自由在全球扩张的趋势,在符合仲裁地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尊重并认可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作出“一裁终局”或放弃任何上诉或司法救济的约定。若当事人已对此此作出约定,则应排除仲裁地法院的撤销权。这一点在美国的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案中得到了适用。第二,对仲裁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理由与执行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理由进行比较适用,若前者与后者相同或类似,则不能复活该裁决;若前者与后者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则可根据本国利益需要自由决定是否“复活”该仲裁裁决;第三,若不存在上述情形,则应判断仲裁地国法院所作之撤销判决是否存在明显不当事由。例如,违反《纽约公约》规定的公共秩序或是否违反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等。
此外,笔者认为,执行地国在考虑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复活”问题时,还应当融入“国际礼让原则”理念,即注重区分“首要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的礼让原则,以增加司法说服力和法院判决的国际正当性。
文章引用
温 顺. 已撤销的商事仲裁裁决域外“复活”问题探究
A Probe into the “Resurrection” of Cancelle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J]. 法学, 2021, 09(02): 254-26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2036
参考文献
- 1. Van Den Berg, A.J. (2010)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nnulled in Russia: Case Comment on Court of Appeal of Amsterdam, April 28, 200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7, 187.
- 2. 董仲英.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探讨[J]. 北京仲裁, 2017(4): 166-183.
- 3. 罗结珍.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附判例解释) (下册)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1200.
- 4. 杜新丽. 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366.
- 5. 美国联邦仲裁法[EB/OL].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asp?id=1071, 2020-06-01.
-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民四他字【2006】第41号[Z].
- 7. Lalive, P. (1976) Les regles de Conflit de Lois Appliquees au Fond du Litige parL’ Arbitre International Siegeant en Suisse. Revue de I’Arbitrage, 7, 155.
- 8. 肖永平, 廖卓炜. 已撤销仲裁裁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2): 49-59.
- 9. Pierre, L. (1999) Why Setting Aside an Arbitral Award Is Not Enough to Remove I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6, 26.
- 10. Paulsson, J. (1997) Rediscovering the N.Y. Convention: Further Reflections on Chromalloy. Mealey’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12, 20.
- 11. Smit, H. (1989) A National Arbitration. Tulane Law Review, 63, 629-631.
- 12. Lazic, V. (2006) Selected Issues: Enforce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Annulled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Croatian Arbitration Yearbook, 13, 179-204.
- 13. Goode, R. (2001) The Role of the Lex Loci Arbitri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7, 19-40. https://doi.org/10.1023/A:1008973626914
- 14. Chan, R.Y. (1999) The Enforceability of Annulled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que of Chromalloy.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7, 145.
- 15. 张美红.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的美国实践及借鉴[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28(5): 76-85.
- 16. 谢新胜. 论争中的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J]. 北京仲裁, 2007(3): 70-98.
- 17. 赵秀文. 国际仲裁中的排除协议及其适用[J]. 法学, 2009(9): 142-148.
- 18. 于喜富. 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与协助——兼论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93-104.
- 19. 张美红. 论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域外“复活”的理据与规则[J]. 政治与法律, 2017(5): 99-108.
- 20. 韩平.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5项的适用问题研究[J]. 法学评论, 2011, 29(3): 77-81.